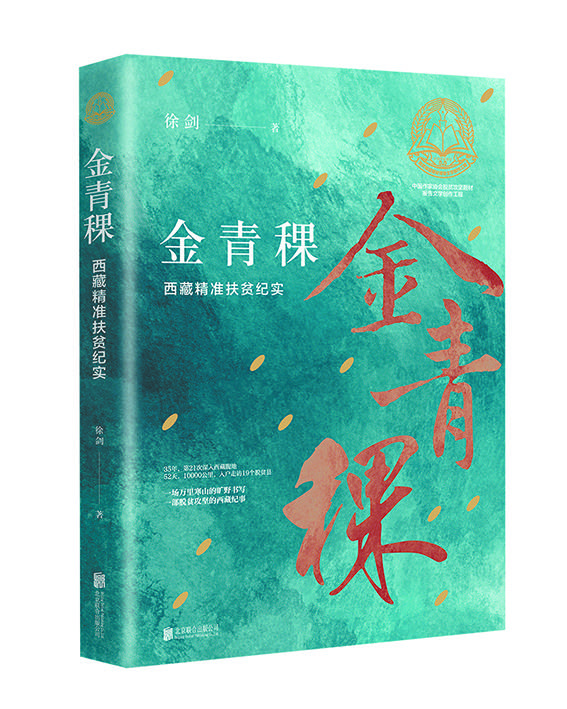本报记者 张丽
日前,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与华景时代推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徐剑新书《金青稞——西藏精准扶贫纪实》。该书是徐剑35年来第21次进藏,在雪域高原深扎52天,走遍西藏最后一批19个脱贫县,采访百余位当地百姓写就,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全景呈现了西藏精准扶贫所取得的伟大成就,诠释了“汉藏一家亲,共筑民族情”的深刻内涵。本报记者专访徐剑,请他来讲述相关创作经历与思考。
记者:为写《金青稞》,您第21次入藏采访,走访多地,克服疫情与高反等多重困难。您说这次采访“翻越的不仅仅是地理海拔,还有文化的、文学的海拔”。为什么?
徐剑:我认为,西藏有三大海拔——地理海拔、文化海拔和文学海拔。西藏有地理海拔。我采访的地方,最高海拔至5300米以上,最低海拔也有3000米左右。我选了一条比较艰苦的线路,从藏东昌都入藏北,环大北线,再从羌塘无人区挺进阿里,转入后藏地日喀则,最后止于拉萨、山南、林芝,在西藏高原走出了一个大圆弧。52天的采访历程中,我遇到了不少风险挑战,我必须从繁华走近荒凉,从都市走向乡村,有的路上遇到泥石流只能徒步翻山,有的路线很窄脚下或车边就是万丈深渊,即使有着多次入藏经验仍要面对高反的各种困扰,等等。但我坚持走完了最后一批19个脱贫县,获得了厚厚的一手资料,痛并充实着。
西藏有文化海拔。想要把握好西藏文化,作家需要具备一定的学识和功力,要有历史学家的深度与眼光,有民俗家、人类学家的维度与科学向度,对西藏历史文化有透彻深入的了解。如果只是用外地游者的眼光或者文化猎奇的目光来写西藏,则有可能管中窥豹、一叶障目,奇书失色。有人问我《金青稞》准备了多少年,我说准备了35年。35年的21次进藏经历,让我对西藏文化拥有较强的认知度与辨识度。
西藏有文学海拔。文学艺术不仅要有高原还要有高峰,所谓文学海拔就是文学高峰。西藏扶贫不能写成与内地扶贫同质化的扶贫,这种独特的书写需要作家跨越时空的边界,抵达生命叙事新的高度,具有民俗文化历史哲学乃至宗教的视野。我开篇写了“东有香巴拉,西有弄哇庆”,这个故事的缘起是,我们到藏北时听说,有人到无人区去寻找像香巴拉、弄哇庆一样的人间仙境。于是,我每走一地,都在问当地人,你们的父辈寻找过白马鉴、弄翁帕龙吗?写完这本书,我找到一个结论是,所谓香巴拉、白马鉴、弄哇庆,不是在梦中,不是在寻找中,而是在创造小康新生活的现实中。党领导下进行的精准扶贫,展现了真正的香巴拉和弄哇庆。所谓文学海拔,我觉得就是这本书是可读的,能够留下来,当后人研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段历史时,能够读到如此精彩、生动的内容。
记者:您在书中记述了很多西藏脱贫路上的人与事,葆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与风土人情。这些给您的写作或人生带来哪些感受与启迪?
徐剑:在采访过程中,我遇到了很多感动的人与事。其中有一位叫坚参的老人的故事至今让我感动。坚参是阿里措勤县达雄乡的一位80岁的老牧民,在2020年1月26日新冠肺炎疫情危急时刻,捐了1万元党费。刚开始我觉得这只是一件好人好事,写不出彩来。可是当我辗转好几个小时艰难地来到边山村牧场,采访完这位个子不高、满头皱纹的老人后,我万分庆幸没有错失这位老人的故事。他原本是一名头人家的放牛娃,1959年西藏平叛时,他赶着牦牛足足走了一个多月,为解放军运送给养。临别时,被称为金珠玛米的解放军给他付了600元钱,嘱咐他说,这是钱,是藏银,不是纸,不能当牛烘引火烧了,以后可以换很多东西。61年后,当国家面临疫情灾难时,这位收入并不高的牧场老人毅然让他的儿子开着机动车行驶两三个小时到乡里捐出1万元党费,他说帮助解放军运输给养的经历使他快速成长起来,成为党的基层干部。当几小时的采访结束时,我拉着老人在他家的黄泥牧屋前留影,看到屋顶上插着一面五星红旗随风飘扬,映衬着这位老党员炽热而透明的初心。当我们的车驶出很远了,我回望过去,老人仍站在小屋前默默招手,那一刻我落泪了,为老人这种赤诚的家国情怀。
我采访了很多“三教九流”的人物,有银匠、铁匠、喇嘛、画师、藏医等。洛加是一名喇嘛,看到寺庙中有人作画,便一心想做唐卡,当成为一名著名的唐卡画师后,他将目光瞄准了贫困户的孩子们,于是办理了唐卡学习班,有四五百人在他那里脱贫。原本在西藏地位很低的银匠,将老家一个村子的30多个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孩子带出来教学手艺,实现了一人当银匠一家脱贫。我还写了一位单亲妈妈与三位大学生的故事。看一个社会文明尺度有多高,就看它如何照顾妇女、儿童与弱者;看一个国家是否真正具有泱泱大国之气,要看它如何眷顾少数民族。通过扶贫,通过政策保障与产业保障让人们过上好日子,“共同富裕”的梦想在党的领导下正在逐步成真与实现。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记者:作为一名“老西藏”,您创作了多部西藏题材文学作品,这次扶贫题材创作您也是选择了西藏,可见对西藏情有独钟。在共筑民族情、讲好民族故事方面有哪些体会与思考?
徐剑:我有三不写——走不到的不写,听不到的不写,看不到的不写。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我写了10本左右,西藏的最多,有8本。
我觉得写民族题材的作品,一定要存敬畏之心。特别是对于西藏高原,任何一个书写者都要有敬畏之心,把一草一木当作自己的眼睫毛一样珍惜。西藏的生态环境太脆弱了,特别是在无人区。因此我在书中写到高海拔搬迁,因为生计,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三个乡的居民搬到文部高海拔草场,而今迁移到雅江边居住,让高海拔草场还给野生动物,逐渐修复生态。西藏是有境界的、有高度的,给弱者以勇气,给自负者以警醒。这种敬畏,不单是点亮酥油灯照亮心灵的敬畏,从梵呗中获得信仰的敬畏,而是与人们的生存与生活链条紧密相连。
要有悲悯之情。这种悲悯,就是要把当地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这也是我一直所提及的在文学创作中要把伟人平民化,平民伟人化,名人传奇化。提起乡村题材创作,很多人都是千篇一律地执着于寻找乡愁与诗意,要么惆怅田园乡村的逝去,要么揭露农村的愚昧落后丑陋等。其实我们更应该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乡村的变化。作家是什么,就是坐在乡场上的篝火旁,给大家讲述这场乡村扶贫的大故事,甚至乡村振兴的大故事,让这个故事照亮心灵、照亮灵魂,给人以希望。
还要有平民视角。我们的写作不应该是说教式或居高临下看待芸芸众生的视角,而应该是平视甚至仰视。只有如此,讲出的故事才一定是独特的,陌生的,生动的。这与一个人的学养、经历,与作家应有的睿智与悲悯、敬畏有很大关系,当然也与作家的文化背景,是否有独特的文化眼光、深邃的哲学思考、纵深的历史背景与视野有关。关于《金青稞》,我写得很从容,很安静,也很温暖,从心灵与脑际走过的阿佳、康巴汉子、喇嘛、银匠、铁匠、画师、单亲妈妈等,这些人物长廊为我描绘了一个时代画卷。每个人都很独特,每个都栩栩如生,他们都是非虚构,完全复原于本真。
这本书是我“盛年变法三部书”的收官之作,其他两本书是关于南海填岛的《天风海雨》和关于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天晓——1921》。三部书完成了我的一个人生阶段,突破了自己,也圆满了自己,让自己的文学稀释,让自己的书写更有人间烟火味,更有思想的高度、历史的纵深与哲学的眼光。
记者:您在跋中提到,扶贫攻坚是对农村题材书写的一个拓展。这对您创作而言具有怎样的意义?在决胜脱贫攻坚之后,这一题材的书写方向是什么?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对于农村题材书写有怎样的影响?
徐剑:关于扶贫题材,我带学生写了关于独龙江脱贫的《怒放》,关于西藏脱贫的《金青稞》,接下来我们还会写一本关于云南百万大搬迁的《安得广厦》。2018年我曾采访下姜村,可以说它是中国美丽新农村的标本与范本,实际上很多年前浙江就开始新农村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这应该也是美丽新农村的一部分。随着扶贫搬迁落地,一座座美丽的新农村,星罗棋布地坐落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一道新的风景线。我们会有新的乡愁、新的乡关、新的家园、新的诗意,这种美丽应该让世界记住。中国作家应该关心的是,对乡村题材书写如何走出千年一面的复调与咏叹,走出新路写出新的创业史。我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参军生涯又与农家子弟朝夕相处,可以说我熟悉中国农民的每一个面孔。《安得广厦》写的就是农民进城以后,他们下一代的命运。怎样写出更有命运感、更有人性深度与温馨感、更有思想和文学艺术高度的好作品,主题出版的故事如何讲得更精彩、更真实、让老百姓更能接受,是我一直关注并探索的。对此,我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