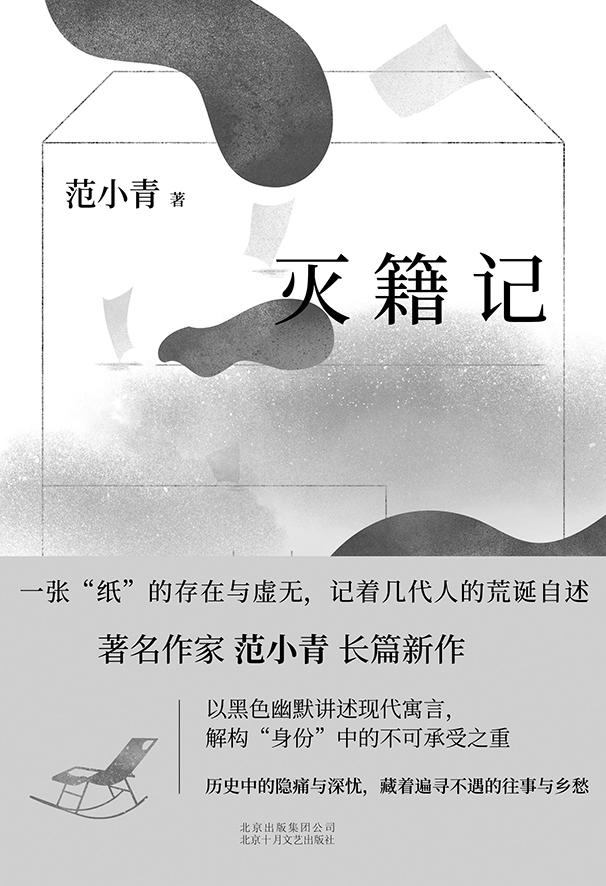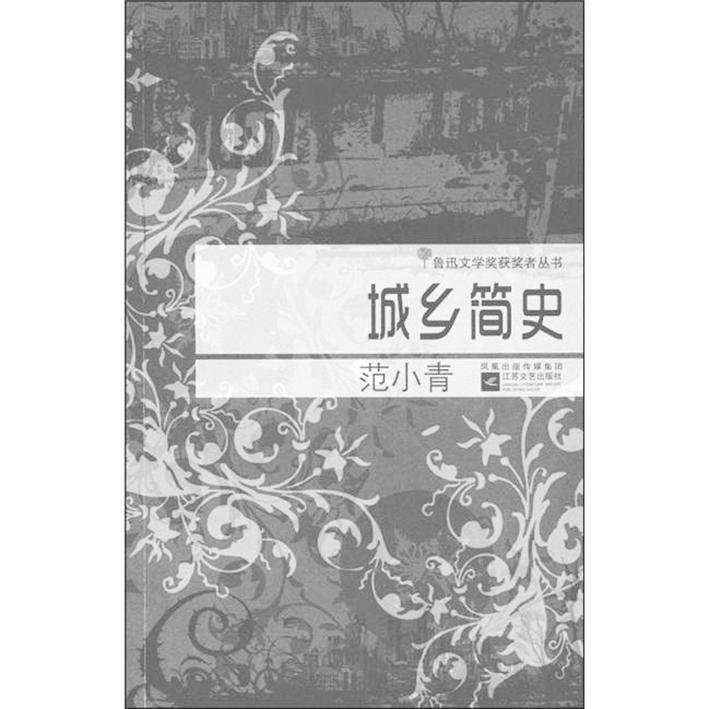□主讲人:李掖平
主讲人简介:
李掖平,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戏剧与影视文学一级学科负责人。山东省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山东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山东文学》《百家评论》原主编,山东省中国现代文学学会、当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莫言研究会副会长。第八、九、十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委。先后出版学术专著8部,合著5部,发表文学研究和影视评论文章50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多项。获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师德标兵、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编者的话:
全国政协读书活动自去年开展以来,已一年有余。各个委员读书群活动依然丰富多彩,委员们参与的热情依然高涨。我们知道,一部作品离不开主题,主题是作品的灵魂与核心。文学作品主题的深入开掘和表达一直是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期讲坛邀请李掖平教授从著名作家范小青的小说创作入手,深入解读了作品中“寻找”这一主题的深刻诠释与精彩演绎,同时,李掖平教授还着重分析了作品《灭籍记》的叙事策略与创作手法。讲解有理有据、丝丝入扣,有高度有深度,给人以想象空间,引人回味,令人深思。
对主题的诠释 对生命的探寻
相信每一个人都和我一样,是从心底深处特别喜欢“寻找”这一具有正能量的语词的。因为这一语词常与真理、未来、光明、希望、理想等联用,其指向表征着心中有梦想、精神有信仰、突破有勇气、创新有力量。因此,一个怀揣寻找意向的人,必定是前行有方向、肩上有责任、心中有使命、既脚踏实地又仰望星空的勇者兼智者。若以此标准来衡量当代作家,我认为作家范小青就是这样的一位杰出代表。从她1980年代的成名作《裤裆巷风流记》,到1990年代的《天砚》《老岸》,到新世纪初期声名大噪的《女同志》,再到2007年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的《城乡简史》,以及到近年来在当代文坛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的《我的名字叫王村》《灭籍记》等,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寻找”,并对寻找主题进行了具有独特标识度的深刻诠释与精彩演绎。
概括说来,范小青笔下的寻找主题涵盖了个体生命从具实性的物质寻找到抽象化精神寻找的方方面面,由此成功塑造了一群孜孜以求、勇敢出发、锲而不舍的寻找者形象,并将一种深刻的哲学思辨气质赋予这些寻找者形象,使其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一群具有独特标示性的“典型形象”,表征出一种现实主义写作的厚度与深度。
如短篇小说《城乡简史》,故事本身讲述的是两个主人公对某种具体东西的寻找,但实际揭示出的却是两个人物对“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一个是城里人蒋自清,捐书时不慎将自己平时记账的一个账本混在其中捐了出去,虽然账本上记录的不过是些自己家日常开支的琐事(如某月某日妻子购买了一瓶拇指大的“香薰精油”,原价679元,打折后是475元,春节前购买一盆蝴蝶兰,原价800元,还价到600元买回来等等),但对以记账来排解日常生活空虚无聊的蒋自清来说,这个账本毕竟是填充自己精神生活,或者说是自己活着、有生存记录的见证,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找回来;一个是甘肃省西部偏远乡下小王庄里的农民王才,因得到的捐赠不是书而是一个账本,在找校长理论继而闹到乡教育办无果后,为了弄清账本里记录的那瓶“香薰精油”到底是个什么东西,查找字典求证不得,继而突发奇想,举家杀入城市,去寻找关于城里人生活和“香薰精油”的答案。小说最后的结局是,蒋自清虽然一直找到了甘肃省的偏远乡下小王庄也未找回自己的账本,但失落的心情却在艰难的长途旅行中渐渐得以排除,重新找回了认真生活的心劲儿;王才带着妻子和儿子举家迁往城里去打工,对城市有了基本的了解,也终于弄清了什么是“香薰精油”、什么是“蝴蝶兰”,感觉到城里的生活到底还是比乡下好。概括而言即蒋自清和王才通过寻找证明了自己的生存并获得了意义。这个故事不仅诠释了当今社会中普通生存承受者的坚忍与坚韧,更显现出作者对生命对生存的一种哲学探寻。
中篇小说《寻找卫华姐》讲述的则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寻找。女主人公“我”(卫华,被同事们称呼为“卫华姐”),有一天被同事小金告知,网上正在热炒一则寻人启事,小金反复提醒“我”就是网上要找的那个“卫华姐”,于是“我”就被扯进了这个找人的故事中。“我”(卫华姐)所经历过的往事(曾与建国、高林一起上学一起工作,后来分开在东南西北,已多年失去联系)和同事小金转告“我”的网事(一个叫鸟人的网民在“老地方吧”上发帖子寻找卫华姐),以及现实中前几天刚发生的一件当下事(高林告诉“我”,建国从外地回来,约我们一起到老地方西七小饭店聚会,但那天晚上“我”和高林等人谁也没有找到那个老地方,谁也没见到谁,聚会因此不了了之)虚虚实实地交织在一起,最后“我”所见到的建国根本就不是老同学建国,因而“我”也根本无法帮助建国,无法为他作证。而“寻找卫华姐”的热点网事,也很快被新的热点所淹没。小说在看似很写实的故事背后,掩映的其实也是一种现代哲学的追问:“老地方已经不是老地方了,没地方可找老地方了”,“你已经不是你了”,那么“我”还是我吗?“我”和“你”到底是谁?这些问题注定不会有明晰的答案,但对这些问题的不懈追问,却恰恰证实了每一个个体生命活着的价值和意义,即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努力地互相寻找并互相认证,给他人一些温暖也使自己温暖。
长篇小说《我的名字叫王村》,寻找的主题看似非常简单,就是“我”丢失了弟弟,然后又试图找回弟弟,但作者却将其写成了一部特别绕人的“寻找自我”的小说,开篇的文字就很是夺人眼球:“我的弟弟是一只老鼠。”随即,叙述者才娓娓道来:弟弟是一个把自己想象成一只老鼠的精神病患者,是全家甚至整个家族的羞耻与拖累,几乎每个和弟弟有关的人都想让弟弟消失。于是,“我”(名叫王全)故意弄丢了弟弟,但终究良心难安又想找回弟弟。故事就在这一丢一找中拉开了帷幕。作者故意设置了类似“我就是我弟弟”“我不是我弟弟”“我就是我”“我不是我”等多条绕口令似的迷径,描绘出现代人迷失自我、想寻找自我又无从找起,甚至根本不能确定自己的荒诞性生存境遇。故事的结尾意味深长,因为弟弟不会表达,所以总是由“我”为他代言,但就在“我”说弟弟不知道自己的名字、签字没有法律效应的时候,弟弟却奇迹般地开口说话了:“我知道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王村。”正是这种有违常理的荒诞或者说吊诡,最终指向了“我究竟是谁?”的哲学命题。
参评2019年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灭籍记》,还是一个与“寻找”相关的故事,只不过这次主人公(吴正好)“寻找”的是自己的身份(寻找和他具有血缘关系的祖辈及其房契)。历史在一次对血缘和身份的找寻中拉开帷幕,作者的眼光在时空中游移回转,审视拆解着轻盈幽默的面纱下隐藏的可笑与荒诞。较之以前的寻找账本或卫华姐或弟弟,这次的寻找身份显然更为重要亦更为抽象。重要是因为我们都是有身份的人,都清楚没有身份在这个社会里是不能存在的;抽象是因为任谁也说不明白,身份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身份与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生命究竟是什么关系,因而其寻找过程无疑就更为复杂曲折,并包含了更多更丰富的信息和意蕴。吴正好在寻找过程中遭遇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人和事,既有因为把档案弄丢了结果被“灭籍”,只能不断地偷别人的身份,最后冒充他人活下去的人;又有事实上根本不存在,完全是被虚构出来的,但因为有“籍”就理所当然被社会认可与接受的莫须有的人;还有一些费劲巴力拐弯抹角想证实自己身份,最后却发现这种证实毫无意义的人。整体说来,它是对主客观时间与空间、现代人主体身份的认知、历史的再现与再认、历史与现在和现实、生与死的终极问题以及叙事本身进行的一次充满黑色幽默的严肃探讨。小说最后的结尾是一个终极性反转,原来吴正好费尽心机寻找的“籍”其实正放在他爸爸吴永辉的抽屉里,时有时无。经过一系列的荒诞遭遇,最后吴正好发现他做梦都在找的那张“籍”,其实不过是一张伪造的房产证明,他只能得到25平方米的房子所换来的利益。一切寻找的结果全部指向无意义,一场梦幻(实际称之为梦魇更为贴切)之后,吴正好面对的依旧是他无意义的游戏生活。很显然,这一看似轻巧的终极反转达到了四两拨千斤的效果,所有“寻找”的意义被全部推翻或者说被彻底否定。正是这种“寻找”叙事的策略性设计,使故事情节在矛盾不断纠结又不断分裂中丰盈丰富起来,历史的隐痛与人生的荒诞、命运的强悍与追求的执着在吴正好的“寻找”中融为一体。
对时代的关注 对人性的悲悯
《灭籍记》给读者带来的阅读感受,笼罩着一种荒诞而诡异的迷雾,这主要是因作者有意设置的“罗生门格局”式叙述圈套所造成的。
作为叙事学的特殊修辞手法,“罗生门格局”是叙事学理论对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的代表影片《罗生门》叙述方式的一种致敬性借用。影片讲述了一宗由武士被杀案件以及案发后嫌疑人之间互相指控对方是凶手的种种事情以及经过。真相只有一个,但凶手、妻子、借武士亡魂来做证的女巫,却因每人提供证词的目的各有不同而各持各的说法,结果人人讲述了一个掩饰自己过失、美化自己道德、减轻自己罪恶的故事版本。于是荒山上的这桩命案,最终成了一团拨不开看不清的迷雾。由此,叙事学界达成了一种共识,认为《罗生门》的叙述方式,便于构设迷雾重重悬念迭起的叙述圈套,能有效增加故事的复杂性和吸引力。
《灭籍记》别开生面的叙述所表征出的,正是叙述全局不可靠的“罗生门格局”。围绕着吴正好寻找亲爷爷及其房契这件事,小说中的所有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判断,每个人的叙述也都是从自我利益需求出发,强调的是他自己认定的所谓真实。因此我们不知道究竟应该听信于谁。甚至连贯穿全篇的叙述人吴正好,都无法确定自己讲述的究竟是真实发生过的真事,还是梦中情景里的臆想。而且他无所事事混日子的无聊行径、慵懒消极的处世态度、调侃揶揄一切的戏谑语气,让读者很难对他产生认同感,亦因此,由这件事牵连出的人是否真实存在似乎都需要打一个问号。既然叙述者本人对于自身发生的事都无法确定也无从解释,那么其叙述也就根本无法被认同或被纠正,一种荒诞而吊诡的生活质感由此而弥漫全篇。
小说采用的是三段式结构,三个部分分别由不同的叙述者吴正好、郑见桃和郑永梅三人以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进行叙述,指向的是叙述者的个人立场和观点而非事实本身,说白了就是三人在各说各话。这就导致了三个部分共同组成的故事情节其实无法联通更无法互相印证。然而三个部分又有情节上的相互交叉,即在故事的内在机理上互为牵连,逻辑上又属于层层递进的关系,于是,叙述的有限真实便因为多个叙述层的分解而更加模糊,最终指向了整体叙述的失真与失信。大故事(吴正好寻找爷爷奶奶)套着小故事(先后找到郑见桃和郑永梅)、故事连着故事的叙事格局,被互为嵌套的三个人各说各话的叙述目的和自我身份的悬疑性细节,拆解成无数个碎片,造成了整体叙述的失真与失信,反射出整个现实世界的荒诞与无以表达。
第一部分叙事人是吴正好,他是探索真相的求证者,亦是建构小说的推动力量;第二部分的叙事人有多种身份,她声称自己是叶兰乡,而真实身份是叶兰乡的小姑子郑见桃;第三部分的叙事人是一个并未真实存在过的郑永梅,其叙述的虚妄不言而喻。同时,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的叙事人之间还形成了对比关系,郑见桃实际存在却没有了自己的“籍”(身份),郑永梅并不存在却拥有合法的“籍”(身份),这两个人物的对照亦充满了喜剧的荒诞感和悲剧的荒谬感。
更有意味的是这三个人的身份、经历所导致的叙述本身就有很多问题,甚至根本不靠谱。吴正好寻找亲爷爷的过程常常出现在他的梦中,一旦事情出现了一点进展或转机,作者便让他从梦中醒来,因此事情发生反转时,就连他自己也无法判断,这究竟是在现实里发生的,还是在梦境中臆想的;郑见桃自从弄丢了自己的档案,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籍”,只能靠偷取别人的身份度日过活的人,在她嫂子叶兰乡去世之后,她便住进了叶兰乡的身份里,以叶兰乡的身份与吴正好对话,对自己的身份她早已习惯于说谎,只有说谎她才能活下去,“我没法不骗人,我的人生最大的也是唯一的习惯,就是信口开河,我从第一次开口说谎,已经过去了大半个世纪了,我早已经习以成谎,早已经没有真话了,或者说,哪句是真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了,我成了一个惯骗”;郑永梅的身份则更加扑朔迷离,他明明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却活在母亲叶兰乡对他的呼喊中,活在叶兰乡为他安排的履历中,死在别人给他开具的死亡证明中。而且这样一个子虚乌有的人,还被作者赋予了第一人称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俯视一切甚至掌控一切。一般来说,第一人称视角只叙述“我”经历和看到的事件,或者说情节发展只能在“我”的视野之中,而作者却大胆创新,将第一人称叙事的视角无限放大,放大到全知全能的无所不知。“既然我不在家,我怎么会知道这些对话。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就是知道。没有为什么。”郑永梅在自己的叙述中根本就不存在,是叶兰乡虚构出来的,但他又是存在的,每时每刻都在参与整个事件,是推动事件向前发展的重要叙述动力之一。
正是依凭这种“罗生门格局”式叙事策略,小说情节得以从容不迫地构设出一个又一个悬念和谜案,慢慢铺陈开那些似真非真的“真相”,将读者带入一个缺少真相甚或根本没有真相的荒诞世界里。“事实真相,那是什么,世上有这东西吗?”随着故事的展开与落幕,一切都在真真假假中兜转回环,我们无可救药地落入了作者设置的叙述圈套之中,根本无法还原历史场景,也永远无法得知真相究竟,关于“籍”的存在、关于三个讲述人、关于其他一干人众、关于历史事件的发生(或许根本没有发生),由此全部陷入“罗生门式”叙事圈套里,成为无解之谜。在小说最后,郑永梅又对自己的身份做出了另一个解释:“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人物,你们别再忽视了,那就是我本人。你们真的认为我只是一个名字吗,你们真能断定我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人吗?”在这种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叙述中,真实和真相距离我们越来越遥远,甚至永远不再。
黑色幽默的间离手法亦是《灭籍记》重要的叙事策略之一。一部经由失真失信叙述建构起来的小说,必然成为一出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闹剧,难怪《灭籍记》封面上公然标明“以黑色幽默讲述现代寓言”。虽然小说故事总体上是以线性发展的叙事(吴正好寻找亲爷爷的线索)方式而展开,但其中不时穿插多位叙述者的历史回忆和现实场境中的言行,话语层面常常造成逻辑上的混乱,这固然表征了作者内心对历史对时代对种种匪夷所思事件的疑问和探索,但同时也凝定成一个贯穿小说始终的模糊含混特征,因而读者无法沿着自己的想象去猜测故事的发展和走向,亦无法探究作者的创作意图,这就导致了小说在叙事模式和叙事手法上的突破与创新。传统的幽默叙事可以在理性范围内去解释和化解,而黑色幽默因为刻意将悖反性矛盾推向极致,从而形成一种无法转圜的局面,以事件的极端荒谬性来昭示人类生命本身的局限与荒诞。
作为一种更加含蓄而且高明的讽刺艺术,黑色幽默就像顶在笑声背后的一柄利剑,笑声越大,痛楚越深,通过或戏谑或讥嘲或反讽等手段带来让人发笑的因素的同时,揭开的是充满了危机和恐惧、痛苦和不幸、焦虑和绝望的生活本质,以间离性的审美引领力引发读者的深入思索。叶兰乡为让自己凭空捏造出的孩子郑永梅获得一张能证明合法身份的“籍”,会每天喊“他”回家吃饭,每天送“他”去上学,将一切话题与郑永梅联系在一起,这个“他”于是在人们的脑海中就成为一个“活生生”的存在。这看起来既滑稽又可笑,但在荒唐的谎言背后是无边的恐惧和焦虑,是卑弱的个体在那个说你是你就是、说你不是你就不是、“真实”完全离场或缺席的特殊时代,对于舆论、对于环境、对于生活、甚至对于一切的恐惧和焦虑。这听起来很是匪夷所思,却恰恰就是那段荒唐历史既荒诞又真实的写照。
如前所述,黑色幽默处处充满着自相矛盾的话语、戏谑的嘲讽和幽默的调笑、悖论重重的结论等间离性叙述手法,必然带来叙事逻辑上的混乱。这种混乱造成了小说的主题属性与风格属性的严重错位。小说的主题是书写历史记忆和关注人的身份焦虑问题的严肃话题,行文落墨间却充满着反讽、荒诞、诡异的意味,处处流露出不正经、无所谓的态度。严肃与荒诞本身便存在着强烈的对比,主题属性与风格属性的严重错位,使小说产生了丰富的戏剧性张力。吴正好在寻找爷爷和房契的过程中会纠结于一些自相矛盾的逻辑混乱,恍如陷入了一个不断循环的黑洞中。比如他要去房管局查询亲爷爷的房产档案时,拿上了一切能证明他身份的证明,却被告知需要提供房屋所有权证,这和吴正好的目的产生了矛盾性冲突:“我就是来找那张纸的,如果我有那张纸,我还来这里干什么呢?”“如果你没有那张纸,我们怎么知道有没有那张纸。”“我要是有那张纸,我还来找那张纸干什么?”吴正好和房管局工作人员的对话让人陷入逻辑怪圈,这就强行中断了故事情节,叙事方向于是被拧歪,逸出正途走向歧路。
这样的黑色幽默剧其实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我们的生活就像这篇小说,既“现实”又“荒诞”,时刻充满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和令人啼笑皆非的意外,《灭籍记》中的故事就是现实中“证明我是我”“证明还活着的我没有死亡”等真实生活事件的文学纪实。“往事就这样清清楚楚地摆在面前了。往事就这样不清不楚地摆在面前了。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也不知道我信不信。”在吴正好兜兜转转的寻找之后,小说最后寻得的不是温情的回忆,而是具有悲剧性的因果。由此,我们发现了历史与现实、时代与个人之间微妙的关系,二者既能互相成就,也能互相毁灭。这是作者对于历史的理性反思,亦是对从历史中走来的人们到达现时代的深切关怀。这种对时代的密切关注以及对于人性的温煦悲悯,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的叙述中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疑惑,同时也带着我对一切的一切的温情”,清坚决绝,锲而不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