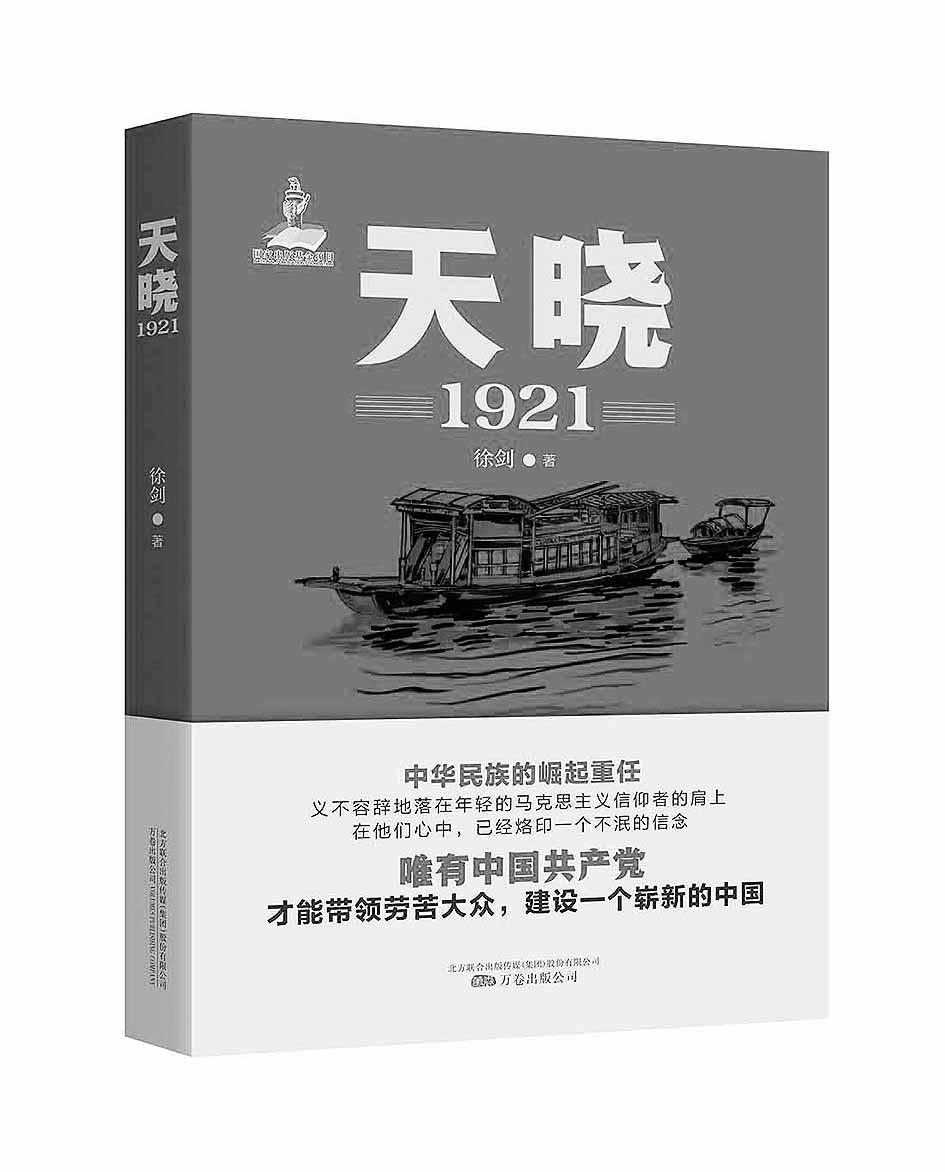徐剑
也许是因为当年毛公润之的身影覆盖了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故对中共一大党史的宏大叙事,多少有点耳熟能详。尽管那些年有些事,由于时代的局限而屏蔽,未能探知历史真相,仅略知一二。但是,随着时间巨流河奔涌,有些记忆渐次模糊了,有些阅读则清晰如昨。因此,当某一天,有出版方邀我写一部党的一大文学读本时,先是愕然,继而肃然,最后欣然从命。
答应写作此书后,我向出版社提出一个额外之请,读书行走,走访13位会议出席者的诞生地、求学地、战斗地、壮烈地,乃至叛徒者的死无安葬身之地,看见别人未曾看到的地方,发觉他人未曾发现的东西,激活未曾觉悟的迷障。这博得对方激赏。我知道,真的要跃入时代的激流,在岩浆运行奔突的烈焰中燃烧一回自己。
半年采访,盛夏入荆楚。唯楚有材,于斯为盛。13位一大出席者,五位出自湖北,两位来自湖南,可见当时两湖天空群星璀璨、英才列列。第一站是应城市刘仁静的老家,住国家电网培训中心,旁边是应城市革命纪念馆。放下行囊,便与该纪念馆馆长相谈,竟不知刘仁静为何人。末了,推荐了一位姓朱的老人,耄耋老人见到我,惊叹,40年了,你是采访刘仁静的第二人。
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其实考古般的田野行走,印证了我的一个创作信条:走不到的地方不写,看不见的东西不写,听不到故事不写。
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我看到他一度也在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跟着体制走,中国已无希望和前途时,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20世纪30年代初,他又远赴莫斯科留学。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夏尺冰头悬长沙城门时,他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最高法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留人,决不错杀一个。长征前,他被留下来打游击,活下来概率几乎为零。江西梅坑,一盘花生米、一壶老酒,他与老友林伯渠别,将实山、实嗣姐妹织的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送战友、上征途,天破晓时,便是生死别离。从此,壮士无归路。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却不敢问两个女儿半句,爹爹可好,是死,是活,还是已经新娶?弥留之际,唯一愿望,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遗骸难寻。我站在何老夫人墓前,恸问苍穹,叔衡老英魂何时能归!
还有董必武,长征时,爱人也不在长征名单内,痴情的妻子一路相送,跟着队伍走了三天,将到五岭时,夫妻挥泪相别。念去去去,五岭迤逦,乌蒙磅礴,一对相爱的人从此天上人间。时隔多年后,董老忆及此,吟一首情诗永记,题毕,顿时老泪纵横。
就这样一路走来,从韶山走到独秀峰。第一晚抵达时,天降小雨,翌日风和日丽,晨曦从韶峰浮冉而起。拜谒毛公铜像时,仰首望天,天边天蓝,那种蓝是哈达般的蔚蓝。我已经多次来韶山了,那天重游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老人家在最后19个小时生命里,看书看文件达11次,加起来1小时50分钟,下午4点30分最后一次阅读,次日凌晨溘然离去,令我辈汗颜。雄才大略从何处来,从5000年文明长河中流淌而出。再看那件72个补丁的睡衣,瞬间让我拂悟,一件睡袍挡百姓风雨、苍生冷暖。
随后10天,我从韶山往独秀峰一路走去,至何叔衡之家,至沅陵窝溪周佛海老宅,然后从怀化坐高铁到重庆,走进江津石墙院陈独秀的最后岁月。一个并不大的纪念馆,我居然安静地看了三个半小时。那一刻,少年碎影中的陈独秀拼图完成了,陈公才华横溢、特立独行,狷介性格,注定了命运悲剧。徜徉独秀园,不由得嗟叹:安庆人民善待自己的儿子陈独秀,以近似本纪的规格,厚葬了他。
行至水穷处。采访结束回到北京,刚写了不到一个月,新冠肺炎疫情始起,我蛰伏于永定河孔雀城,伏案五个半月,每天从早晨7点写至子夜时分。到4月上旬,免疫力下降,患上带状疱疹,腰缠半边龙,痛了一月之久,各地的亲朋纷纷给我寄药,解我小恙。当31万字《天晓1921》落下最后一个句号时,喜极而泣。10天会期之瞬,写尽百年沧桑,追随13位党代表身后踽踽独行,经历一场炼狱之旅。推开窗子,时春光明媚,百鸟啼鸣,铁栅栏蔷薇花正盛,生活多么安静美好。远天中,南陈北李与13位一大与会者向我走来,青春与梦想,初心与信仰,忠贞与背叛,牺牲与尊严,壮丽与沉沦,皆还魂归来,跃然纸上。故国神游,积贫积弱不再。百年人生圆一梦,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天晓》从采访至杀青,耗时1载,书稿备案审查,又历时1年半。欣慰之余,我觉得自己拿到了一张党史、国史写作的入场券。感谢行走采访中相助的刘克兴、王跃文、纪红建、王丽君、韩生学、向显桃、李银德先生,慷慨以助,还提供不少孤本绝版。
“天晓”一词,取之庄子“天地”篇“冥冥之中,独见晓焉”之意,摩挲飘着墨香的新书,想到董必武携夫人1964年清明节回到嘉兴,坐画舫,登上湖心岛,伫立烟雨楼,题下“作始也简,将毕也钜”,仍为庄子所语。
2020年5月15日发走书稿,一段红色之旅画上句号,令我此生无憾。“壮年变法”三部曲之第二部落幕,就像打了胜仗凯旋的士兵,交回令牌,等待下一次出征。
10天后,我又去了西藏,去收割《金青稞》。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作者系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