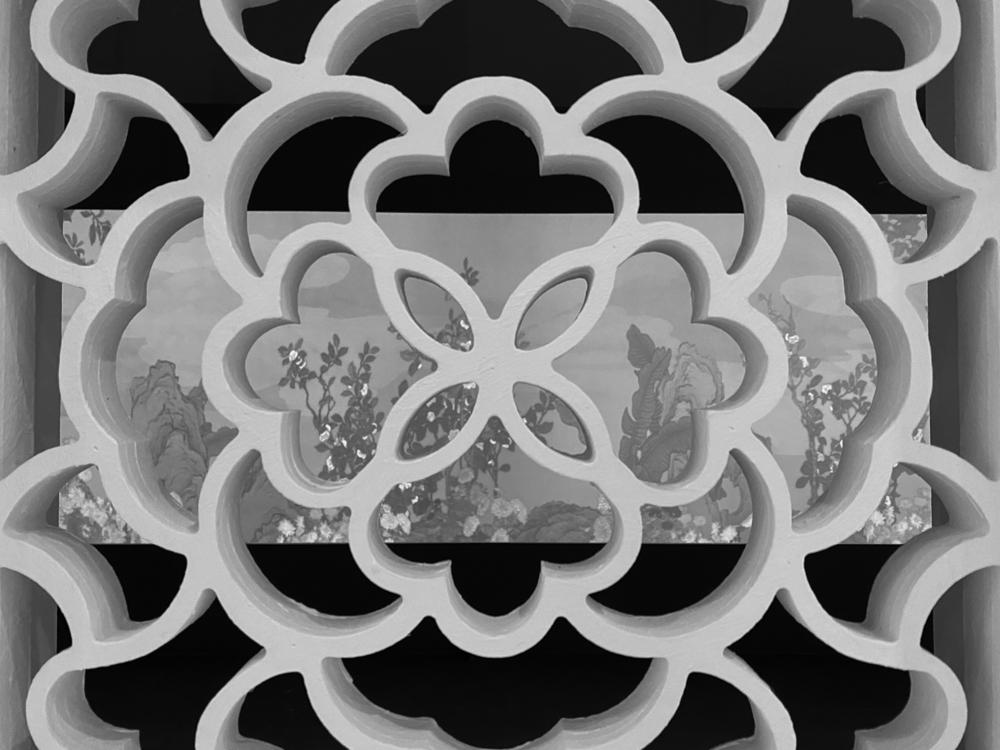□主讲人:吴洪亮
主讲人简介:
吴洪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画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编者的话:
中国是诗词的国度,中国园林历史悠久、渊源深厚,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都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吴洪亮是著名艺术策展人,其工作主要是在研究的基础上,将艺术作品或文物进行遴选、分类、排列组合,进而在博物馆、美术馆或一些公共空间中建构一个情境,与公众分享。
作为一名策展人,吴洪亮认为,从展览到词与园林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用两对词语来描述:一对是有限与变化,一对是生活与美感,它们都是在有限的或限定的空间与结构中求变化,也是在生活与生命的各种体验里生发美的感受。近年来,在他的策展工作中,有很多机会把中国园林与中国诗词加以印证,从中也理解了中国著名古建筑园林艺术学家陈从周所提出的中国园林是“综合艺术品”的意味。本期讲坛是吴洪亮委员在全国政协“国学读书群”第八期委员读书活动中的演讲,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与谁同坐
苏州拙政园里有一座依水而建的扇形“与谁同坐轩”,这个名字源于苏东坡的《点绛唇·闲倚胡床》。词的上阕是“闲倚胡床,庾公楼外峰千朵。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写自己虽然独处楼内,却与天地自然同在。苏轼是个阔达的人,他的《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有很大影响,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即使在窘境之下,也写得气势奔放。这里他写“明月清风我”,一派安适,人与景合为一体,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这不仅是词境的追求,也是造园的追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讨论词的“境界”时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
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写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
不仅填词如此,为了在有限的小空间里营造出自然宇宙的无限遐想,园林发展出了借景、对景、引景等各种艺术手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诗词之境,也是园艺之境。可以感受到,园林与诗词分享同一套审美准则。
景题也是手法之一。再说拙政园里这个“与谁同坐轩”,虽然没有点出明月清风,但是了解出处的人自然会心一笑。东坡这首词还有下阕,“别乘一来,有唱应须和。还知么。自从添个。风月平分破。”笔锋一转,来了朋友,从独处到与友朋唱和,各有其美。这样层层展开的深意,给园林景色带来无限魅力,试想月色清华的夜晚,临水而坐,或独享静谧,与清风明月为伴;或契友在畔,平分风月。
不仅如此,“与谁同坐”何尝不是在追问一些更根本的问题,“我”是谁?“我”与谁把臂同游?“我”为什么要与清风明月相交?为什么“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园林为什么要追求方寸大千、咫尺万象?苏轼评陶渊明的诗“因采菊而见南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为什么境与意会、心与境合就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宇是空间,宙是时间,也许,在园林里坐看四时变化的中国古人,是在融入自己的天地宇宙。王国维说“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世界与我情景交融,“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我已与世界融为一体。
之所以从这个“与谁同坐轩”讲起,跟我们曾在拙政园里设置过的一个“驿亭”装置有关,也与我们今天的人“与谁同坐”的问题有关。2019年,我有幸策划了第58届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中国国家馆的展览。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被称为国际艺术界的奥林匹克,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May You Live in Interesting Times)。当时正处于一个全球化进程出现壁垒的时刻,结合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想借展览传播中国文化中的智慧,并回溯一些人类文明更根本的共性。
“Interesting”这个词在此处有特别的寓意,指向今天人类发展面临的新问题。而解决当下与未来的问题,很多艺术家与学者倾向于从人类过往的发展中寻找一些启发,这些回眺的状态,后来成为记载在历史学家笔下的“复兴”或者“复古”,中西方历史中曾多次出现这样的现象,而复归的浪潮中必然也伴随着新风尚的爆发。基于这样的逻辑,我选择了四位艺术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分别从文明的共识、生活的日常、自身的感知三个维度呈现了艺术家们“Re”的探索。“Re-睿”的主题试图强化因为“Re”所以“睿”的概念,这也是当代艺术思考的一种方式。
在策划过程中,发现这座西方的水城竟然与中国古城有极多相似之处,无论是水道与桥,还是北京的胡同、苏州的弄堂,或者威尼斯的小巷,这些时疏时朗的空间关系和似曾相识的城市意象,既有园林之美,也是一首空间中的诗词。因此,决定了我对展览空间的构想。展厅的空间节奏如同一幅中国画的立体长卷,它的有趣之处在于不能一览无余,时而逼仄,时而豁然开朗,只有漫步其中,用心体会,方能感悟。这也有赖于中国园林的一个妙处:没有唯一的重点,移步换景,每个位置上都有独一无二的主角。参展艺术家的作品就像园子里的亭台楼阁、树木池塘一样,每一件都是这个位置上最恰当的主角。
由于希望展览把这些思考带到更多人的生活中,借助艺术视角重新构想未来的可能性,因此,与威尼斯双年展同步,也在国内多个城市建立了分享信息的“驿亭”,中国古代专门建立有传递信息、文书,供旅途食宿换马的驿亭。“亭”者,停也,是供旅人停下来休息游憩的地方。“驿亭”让没有到达威尼斯的观众同样能以不同的方式体验展览。其中设立在苏州拙政园内的“驿亭”装置有一对形如倒影的门,一为上圆下方,一为上方下圆,化用了拙政园中“与谁同坐轩”的苏作风格。因为这届威尼斯双年展的主题是“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因此我们为这个驿亭取名为“与谁同趣”,呼应拙政园中这座轩亭,寓意威尼斯、苏州与每一位来到驿亭的“我”同趣。
拙政园西邻,是由现代主义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苏州博物馆是综合性博物馆,虽然藏品以出土文物、明清书画、工艺品、古籍善本见长,但有非常好的当代艺术积累,这是贝聿铭先生定下的基调。2006年新馆开馆,贝聿铭在完成建筑设计的同时,站在博物馆未来发展的角度,建议设立现当代艺术厅,我曾在这个现当代艺术厅为中国画家丘挺做了一个名为“延月梳风”的个展。依然邀约了苏轼的明月清风,题目四个字来自拙政园中的两扇月亮门,二门相对,一名“延月”,一名“梳风”。
早在2005年,丘挺就开始研究各处园林,并以之入画。中国的园林,是人工与造化、人文与自然的综合载体。造园本就是一种艺术化的空间处理,丘挺以园林入画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再次艺术化表达。为此展,“与谁同坐”成为丘挺最新的园林创作,也集中呈现了他近年来的山水风格。此画描绘的是拙政园的与谁同坐轩,但细细品味则会发现,艺术家并未一板一眼地按照对象进行写生,而是构造了一种全新的画面关系。作者就像超级英雄“奇异博士”一样,可以随意进行空间的转换,将平地之上的庭轩置于山丘,原本的楼阁建筑也被重新安排,全然是一番新的景致。
沧浪之水
诗词与园林都是中国文人生命体验的一部分。中国的哲学思辨始终与日常的物质生活和审美生活紧密相连,就像朱熹所言:“道,人伦日用之间所当行者是也。”林语堂总结为“生活哲学”,他分析“产生这个生活哲学的中国人的理智构造——伟大的现实主义,不充分的理想主义,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对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诗意感觉性。”对于这“不充分的理想主义”,他解释“理想主义的成分如果太多,于人类颇为危险,它使人徒然地追求虚幻的理想”。于我而言,在宋词与园林中,我看到了中国人是如何在现实里开辟出一片安放自己人格理想的天地。
沧浪亭是苏州现存最古老的始于宋代的园林。其地宋初就被中吴军节度使孙承祐营建为别墅,但名声大噪还是在苏舜钦之手,因有感于渔父对屈原所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命名为“沧浪亭”。从这个园子的名字我们可以窥见一条藏在园林背后的线索——中国的隐逸文化。
跟屈原对答的渔父无疑是一位隐士,以一个智者的形象出现。隐逸思想为士大夫们保持独立的思想和人格提供了精神庇护,然而像渔父这样隐于山林的生活却过于困苦了。白居易有一首题为《中隐》的诗里写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白居易的“中隐”提供了一个利于执行的解决方案,在苏舜卿生活的两宋时期得到弘扬,苏轼曾写“未曾小隐聊中隐,可得长闲胜暂闲”,有人的园第名叫“中隐堂”,从现在依然存在的园林“退思”“拙政”这些名字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园林在“入世”和“出世”之间提供了面对世界的方法和态度,以及面对问题和矛盾时的解决方式。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异同,都在这方芥子须弥的小天地中循环。
所以,园林的妙处在于那份诗意空间的背后是“出世”与“入世”矛盾中的物化。它不仅是安放“身”的,更重要的是安放“心”的地方。基于这样的理解,我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策划了“自·沧浪亭”的展览,“自”有两层含义,既指从哪里来,也隐含了到哪里去。在这个展览里,我开始深入理解园林对于人精神与心灵的意义。秉承周有光先生所说的“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我们尝试从全球化的眼光、从更多元的角度来看待园林的丰富性。当苏舜钦为他的园子定名“沧浪”时,就为沧浪亭的空间意义确立了内在静观、自我存养的基调。“沧浪”的精髓在于以一种超然的情绪,寻找进退的平衡点;这个园子的精髓在于以一种文人的性情,于尘世间造就一个有如平行世界的世外桃源,为外部世界和自我心灵之间构筑起身心自如的缓冲空间。这并非是妥协中的自洽,而更像苏州人性格中的“糯”,仿佛绵柔但难以让其折服。在中国文化的漫长积累下甚至演变成一种入骨的情怀、悲观中的惬意。因此,走入园中虽会有处处用心、步步小心的感觉,但内含生机与活力,甚至不由自主地让人打开所有的感官,迎接微风、细雨、草香、鸟鸣……进而享受迷失的快感,绝无日本庭院带给人的那份“寂”的寒意。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或许可以说园林带来了心灵上的疗愈。现在,园艺疗法已经被很多研究证实,其在修复注意力、平稳血压等方面的有效作用。当然,园林的整体意涵远不止于此。所以,在这个展览中我邀请了心理学、哲学、历史、建筑、音乐、中国书画、当代艺术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它们虽然是独立的学科,但中国传统园林恰恰是个“交叉点”。琴、棋、书、画、诗、酒、茶,我在之前的另一个展览“自·牡丹亭”中所关注的昆曲,也都与园林有关。在这个态度下,以这样全球化、多学科的视野进行研究,其实反而回到了中国园林的根基。由于这一展览联合了中外艺术家的相关作品,得到了多方关注,并获得了当年文旅部评出的全国十个优秀展览之一。
苔石梅窗
某种意义上来说,填词、造园异曲同工。从创作过程看,填词有格律,句子长短、音调、韵脚都有规则限定;园林则受场地条件、工程技术、植物习性等各种因素制约。从审美原则看,由于文人在造园活动中逐渐提高的参与度,造园也与诗词、绘画分享同样的审美标准,讲究韵律节奏、求曲不求直。可以说,无论是填词还是造园,不管用文字还是综合手段,创作者都在试图全方位地调动读者或者游览者的感官体验,调动人们的眼、耳、鼻、舌、身、意一起参与到审美情境的建构中来,感官体验是“境界”的基础。无论是填词还是造园,都离不开基本的构成要素,而这些要素很大程度上是相通的,园林与词互相影响,词描绘园林的景象,园林造词的意境。如果要说哪里将这种相互影响描述得最为清晰,首先想到的便是明代文人撰写的生活美学指南,尤其是文震亨的《长物志》。
“长物”二字,从读音到意思充满了纠葛。对此有人做过专门的研究:有两个读音,一个读作cháng wù,意思是“好的东西”,清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土地庙》:“市无长物,惟花厂鸽市差为可观。”另一个读作zhàng wù,意为“多余的东西”,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王大)见其坐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长物志》中的那些“长物”是多余之物,还是“文震亨们”生命中的必需之物呢?这其中的复杂性难以厘清。
继“自·沧浪亭”后,隔年我又在苏州金鸡湖美术馆策划了“自·长物志”,这一展览不只讨论那些所谓的古雅之趣,而是在“格物”的逻辑下,探求更多物与人、物与社会、物与历史的关系,甚至是“物”之于世事、人心的反作用力。因为这次全球疫情“提示”我,此展于当下并非是一个轻飘飘的话题。尤其是作者文震亨,作为明四家之一文徵明的曾孙,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对于他能写出《长物志》这样的书,并不感到稀奇。但当清兵逼近,他却投河自尽,自尽不成,断食而亡。这样一个养尊处优的人,为何能如此决绝?这虽不是个案,也是当时很多遗民的选择,但还是令我想到了伯夷、叔齐采薇时的场景,想到了屈原与渔父对话时的尴尬,想到了王国维在昆明湖自尽时的状态,想到了梁漱溟的父亲说出“这个世界会好吗?”那一刻的惆怅。文震亨的决绝,使《长物志》这本书平添了几许悲剧的能量,也使我对于展览的厚度有了新的考量。
这一展览里有一个观察那些由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论述而引发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的趣味及其变体的部分。展厅入眼便是陈琦巨大的作品《天界》,此作以曾为文震亨兄长文震孟所有的园林艺圃为蓝本绘成,横亘在展厅中,酷似艺圃中纯粹、平直的延光阁。“天界”其实在人间界,园林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聚会,是种种试图浪漫的过法,人们对天界种种美好的想象,都像被映射到园林生活中。遗绪至今,那些趣味的样貌变了,但总能品出其中似曾相识的遗传基因。“天界”前是黄钢的“太湖石”装置,这一意象与园林的早期建构有关,也使我想到了当年宋徽宗所造皇家园林艮岳的花石纲遗石。与“天界”里观赏其“正”形的太湖石不同,这件装置意在关注石头的“负”形,一阴一阳的转变,形成过去与现在错综的时空感。太湖石一侧有梁铨专为展览创作的三件作品《紫藤花下》《幽致》《苔(阶有苔斑者为佳)》,呼应着文徴明手植于今日苏州博物馆的紫藤,“淡语皆有味,浅语皆有致”的青竹,“阶有苔斑者为佳”的那片隐约秀绿。
“苔”在文震亨的评价标准里是不可或缺的:
自三级以至十级,愈高愈古,须以文石剥成。种绣墩或草花数茎于内,枝叶纷披,映阶傍砌。以太湖石叠成者,曰涩浪,其制更奇,然不易就。复室须内高于外,取顽石具苔斑者嵌之,方有岩阿之致。
阶上苔痕引人想到山野林壑之美,就像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宋代词人也有很多笔墨来写苔,“庭院深沉绝俗埃。绿苔因雨上层阶”(陈德武《浣溪沙》),“心事一春犹未见。红英落尽青苔院”(欧阳修《蝶恋花》),“径苔深,念断无故人,轻敲幽户”(吴文英《探春慢》)。苔是内敛的,苔在长久的安静和清冷里长得更好,因而天生就带上了情绪,以至于可以影响评点梅花的品性,“我亦。几时得。归检点苔封,评品梅格”(李曾伯《兰陵王》)。这时再回看梁铨作品青碧的色调,别有一番感慨。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实践,即便图像的风格不一样了,画里的诗意从未远去。
北宋的画家郭熙在《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写道:“世之笃论,谓山水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画凡至此,皆入妙品。”对园林而言,它本就是可行、可游、可居的,但“窗”大大延展了可望的空间。“窗”是诗词、园林乃至中国画中共享的元素。
2021年,在受中国园林博物馆之邀三年后,我策划了一个名为“窗,园林的眼睛”的展览。选择“窗”这个主题,最初由于园林中的窗主体造型之美,其作为特殊的空间的媒介,将主客关系、虚实关系、内外关系、功能与美感,处理得恰切而出人意料,又归于情理之中。每每赞叹之余,还会引发对当下生活的思考。窗,不仅仅是形式、功能,甚至是意义的眼睛。而古人笔下的“绿窗”与“寒窗”,不仅有“一枕小窗浓睡”的快意,也有顾城笔下“我想在大地上画满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习惯光明。”让人每每读来,皆会泪水溢出。窗,成为生命另一种价值的象征。
中国园林是多维的,窗亦是如此。我们团队在这次展览前期的研究中发现了古人在制窗工艺中暗藏的有关“幂”的理念,让大家惊艳于几何的美感,从而生成了展览的空间与视觉的设计,在此展览里,我们把木作中的“六幂基线”作为展厅的基本模数,空间划分只能在“六幂基线”上增减,就像填词一样,我们为空间设计规定了一个“词牌”。
选取“窗”这个园林中的细节,展开多维度的探求,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与生活的一次再思考。园林是一门综合艺术,将建筑、书法、绘画,甚至文学、戏剧、音乐等门类集于一体,为精神生活提供了特殊的情境,与中国独有的生活美学一脉相通。而窗是园林的“眼睛”,在满足流通光与风的基本功能之外,更在园林造景中衍生出借景、框景、对景、漏景等许多巧妙的用途,形成别样丰富的趣味。汉代刘熙在《释名》中解释:“窗,聪也,于内窥见外为聪明也。”可见,除了功能之用,“窗”更是中国人观看方式和审美趣味的巧妙外化。
展览也是我的“窗”。透过策展我读到了词与园,何为有缘?就是不期而遇,就是初见反觉“旧相识”,就是百读不厌,就是“不思量,自难忘”。这就是我在策展过程中体会的词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