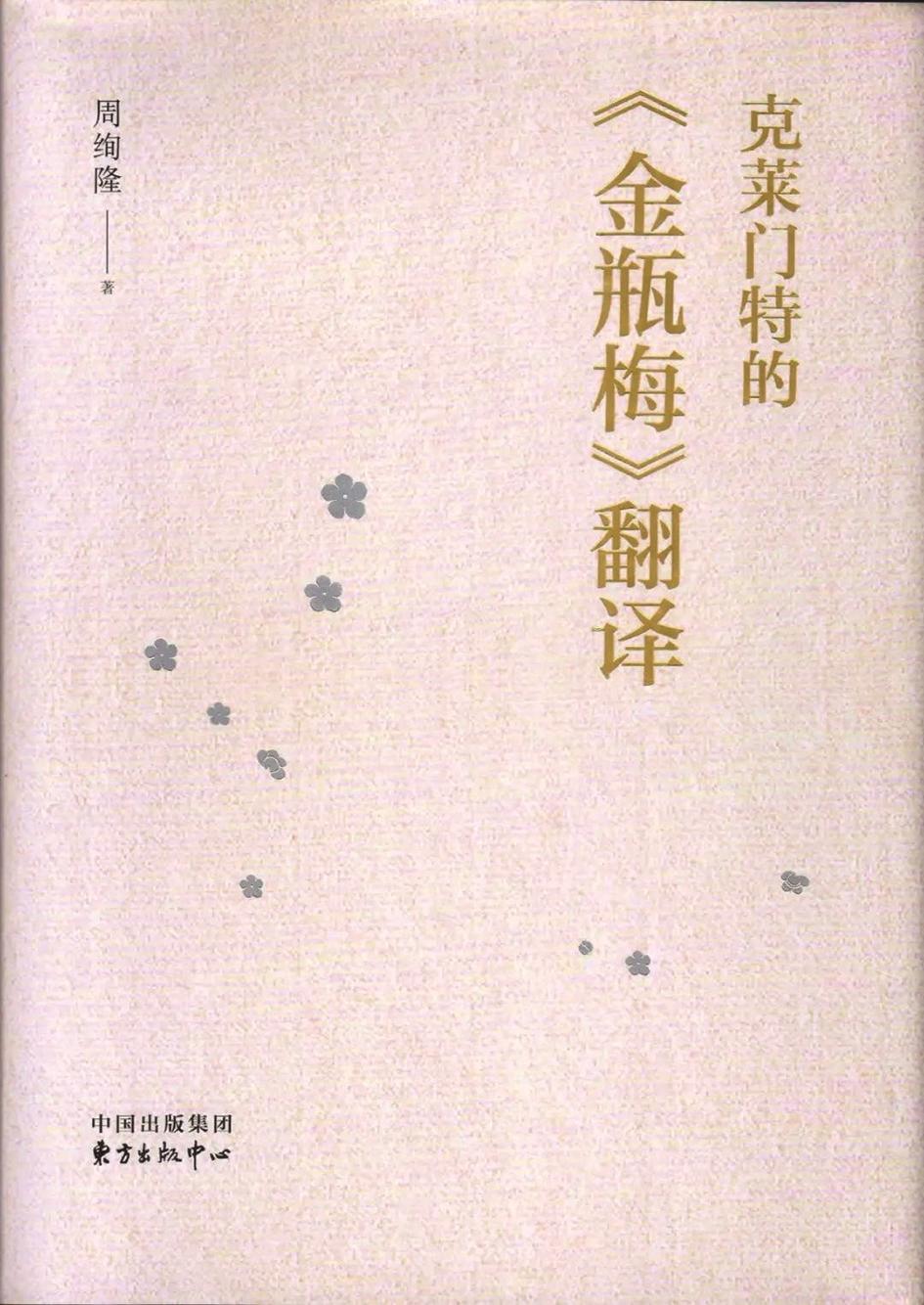李晶
一个多月之前,《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摆在我面前。捧着这本装帧雅致的小书,一则新鲜,二则恍然有旧友重逢之感。书诚然是新书,但书里的好些内容,我听作者絮絮叨叨已将近10年了。印象最深的是他早年念念不忘对“光阴如梭”“白驹过隙”等俗语翻译策略的评批,以及对书中一些“译错了”的细节的挑剔。我本人多年来一直在《红楼梦》的杨宪益、戴乃迭译本和霍克思、闵福德译本之间爬梳比对,感叹译事之难和优秀译者的精彩表现之余,常替他可惜:这么好的中英文功底,不去鉴赏经典译本的精彩之处,枉抛心力做批判。但他显然乐在其中,另外也是责编的职责使然。翻遍全书,基本可以看出,他积攒的大量错译误译的例子,读者不会在意,译者本人也不在意,甚至原作者倘能再生也未必会如何介意,但身为要对读者和质检有所交代的责编,尤其双语对照版图书是最不能包容错误的,很多误译之处他确实不能不理。
书稿的基础就是作者十几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做“大中华文库”中英对照版《金瓶梅》一书责编时留下的编校记录,在此基础上他查访许多资料,梳理了《金瓶梅》在英语世界里翻译和出版的历史,写成两篇长文,也就是这本书里的“《金莲》的翻译、出版与修订传播”和“《金莲》的翻译问题考察”。这是两份沉甸甸的文献,尤其是对《金瓶梅》翻译史的爬梳,以及对《金莲》一书翻译情形的推断。译者克莱门特在译本卷首向老舍先生郑重致谢,但据本书作者考察,老舍对于曾经参与外国译者的《金瓶梅》翻译三缄其口,从不提起。他在其中究竟起到多少作用,是一个有趣的难解之谜。《金瓶梅》公认的最佳英文译本是美国学者芮效卫翻译的五卷词话本,从第一卷到第五卷的出版时间绵延至20年(1993-2013),而译者在第一卷卷首坦言,此卷出版前他已经在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上耗费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精力——早在1985年,香港的《译丛》杂志上确已发表过芮效卫对《金瓶梅》一些章回的翻译和相应的研究文献。相形之下,《金莲》的翻译时间要少得多:“据他自己说,他大概是从1924年开始翻译这本书的,翻译用了五年,对译稿打磨修订和处理校样则耗了近十年时间。”大概老舍先生确实帮了他不少忙吧。
我国读者普遍将小说作为消遣读物,但在多数外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眼里,中国古典小说的价值和地位很高。他们从《红楼梦》和《金瓶梅》《儒林外史》里认识明清时代中国人的言谈举止,了解古老中国的园林、服饰、医药、饮食、文玩、官场上下、三教九流,像是近距离观赏一部连台大戏,不知不觉就会沉浸其中,既被优雅细腻的艺术内容所吸引,也为封建黑暗的现实而动容,忍不住动手将它翻译成本国文字,介绍给母语读者。邦斯尔(彭寿神父)和霍克思译《红楼梦》的英译本、松枝茂夫和伊藤漱平译《红楼梦》的日译本、雷威安译《金瓶梅》《聊斋志异》的法文译本莫不如此。《金莲》的译者与这些翻译家相比略显轻松一些,从他的译者自道和对译文的处理方式来看,他都没那么在意原著的“神圣”与“完整”,也因此形成了自己的翻译风格:大胆删削原文,时常调整对话人物甚至是对话内容,语词、断句和数目等方面的细节错误不断,但整体而言是一部语言流畅、节奏鲜明、画面感很强、非常能吸引一般读者的优秀译本。
对于《金莲》译文的传神之处,《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一书中总结了寥寥八条;但对译者所做的删削和犯下的“错误”,则从“认字”“断句”“成语俗语歇后语”的误解到省略、漏译、“人名人称”的误译等多方面,整理出10个章节的内容。不仅如此,作者还总结出一个很有规律的现象,那就是有些错误,在书中前面一些章回里都是译错的,到后来一些章回却译对了。这是否说明,随着对一些词汇或俗语习语见识的增加,译者后来理解了正确的含义,在译文中有所调整,只是没有回去在前面的译文里重新捉一遍“虫”?从其他名著的一些经典译本来看,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并非独例。举世公认的中文英译大家霍克思先生晚年亲自修订《石头记》译本,前两卷章节里有些细节的错误,香港翻译大家宋淇专门撰文著书指出过的,他也并未改净——事实上,虽然霍克思非常感谢宋淇对他译文的关注与批评,但宋淇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误,比如著名的“怡红”与“快绿”之争,再如贾府和大观园里一些花鸟的细节乃至诗词中的删削,他都没有改。翻译家大多是倔强的。
既然是责编手记,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自然是对《金莲》译文错误的总结与分析。从头至尾看下来,错字、断句、成语和俗语谚语方面,作者目光如炬,所指出的绝大多数“错译”都是实实在在的错误,有些甚至是辨认字形不够准确造成的,如“狼”与“狠”之别、再如“不差甚么”误解成“不羞什么”,这种毋庸多言;比较有趣的是成语、俗语与歇后语的翻译“错误”,书中举出的一些例子,在不甚熟悉古代俗语的中文读者看来,也颇为解惑。
《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中指出的另外一种“误译”,是译者在行文中张冠李戴,将对话或叙事中的人物弄混弄错,如春梅和秋菊的混乱、孟玉楼和吴月娘的混淆等,这些批评都是准确的;但作者批评的《金莲》里另外一种常见的情况:译者将对话人物另行调整,原著里某些说话人在译文里成了另外一个人,言谈内容也相应地有所变通,这种应该不属“错误”,而是译者为了照应中英文表述习惯差异而做出的技术处理。原著七十九回里冯妈妈和西门庆、王六儿的对话即是这种情形的一个典型例证。
中国古典小说在西方语言里的翻译一直是大有难度的。难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也难在许多文化内容的此有彼无,不知从何译起。《红楼梦》的保加利亚文译者韩裴就曾撰文感叹,“翻译《红楼梦》最主要的困难在于曹雪芹小说中蕴含的极大丰富的文化知识,犹如百科全书一般”。无论是人物角色及其姓名自带的种种象征,还是传统的中国植物、药材、建筑术语乃至服装、饰物等等,在保加利亚文里都没有对应的词汇。译者或用音译加注,或想尽办法在母语文学里寻找资源移花接木,都是需要大费周折的。《金莲》的译者面对《金瓶梅》,遇到的困难不会少到哪里去,他在翻译过程中的删削与“错误”,至少也是可以理解的。
翻译的一大难点也在于古代俗语的理解之难。不要说外国译者,即便是我们本国的学者,也难免偶有望文生义或不得甚解的情形。启功先生谈到他为《红楼梦》做注释时遇到的困难,曾举过一个例子,那就是在《金瓶梅》和《醒世姻缘》中也出现过的“不当家花拉的”一词。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注释《红楼梦》时曾以为是“不了解”的意思,后读明人刘侗《帝京景物略》才知道“不当家”即是“不应当”“不应该”的意思。“家”是词尾,“花拉的”是这个词的附加物,是为增加这个词的分量的。汉语的词汇浩如烟海,本国的资深学者尚且容易出错,对于西方译者在翻译中的错失,我们似乎不必过于计较。毕竟《金瓶梅》这样一部长篇小说译成活灵活现的英文,大量古老中国的市井人物和他们的悲欢离合得以传达到另一个语言世界里,吸引着西方大众读者了解中国文化,这已是值得赞赏的一项成就了。
长期以来,我们的批评家都倾向于挑剔汉语典籍的外语译本出现了哪些错误,这是一种传统。翻译是不可能不出错的,有些是译者的大意或能力不逮所致,但原著内容在另外一种语言里的许多删改与变形,主要是因为译者的目标读者并非能阅读外语的中国人,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而只需要一个精彩故事的外国人。就此而言,《金莲》的译者还是比较称职的。他会被专门著书批评得这样透彻,应该是生前万万想不到的,如果他泉下有知,大概会像霍克思先生面对宋淇的批评一样,既感叹又感谢吧:
“身为一名外国译者,译作要经受中国专家如此通透的审阅,多少有点惊恐;同时又为这样受重视备感骄傲和满足——译文中不管有多少偏失或错误,竟然引起如此关注……不过我觉得凌驾于其他一切感受之上的乃是感谢——如果宋先生不反对,不如说这是一种‘同道之谊’——放眼所有读者,我确信宋先生是知我者。无论赞同还是反对,他总明白我做了些什么,或努力想做到什么,而且知晓我为何如此。得到理解胜过得到赞美。”
周绚隆此著对于英文版《金莲》的意义,大致与此相类:认可这是一部优秀的译作,倾注大量精力去知晓译者的努力及其成败,虽然纸面上的赞美不多,但胜在尊重与理解——真挚专注的批评是另一种形式的赞美。
(作者系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