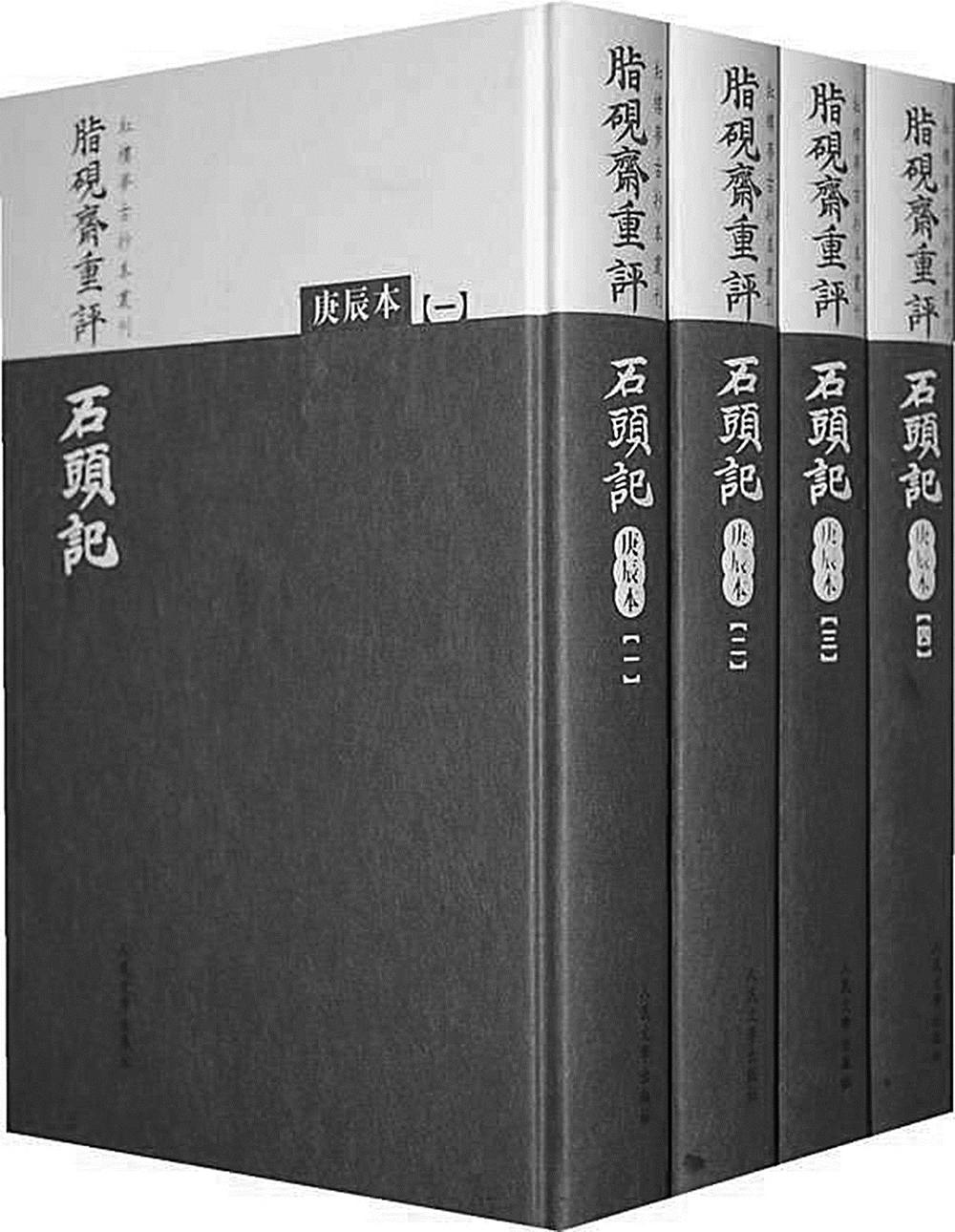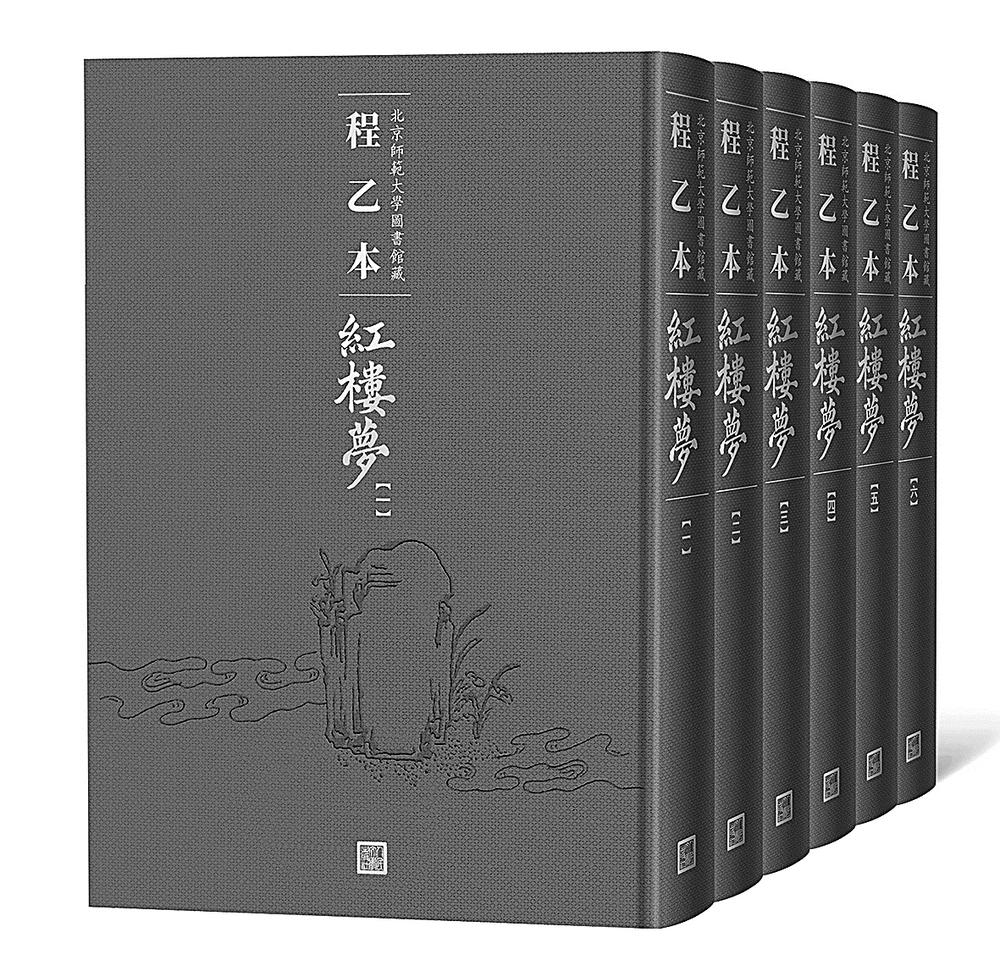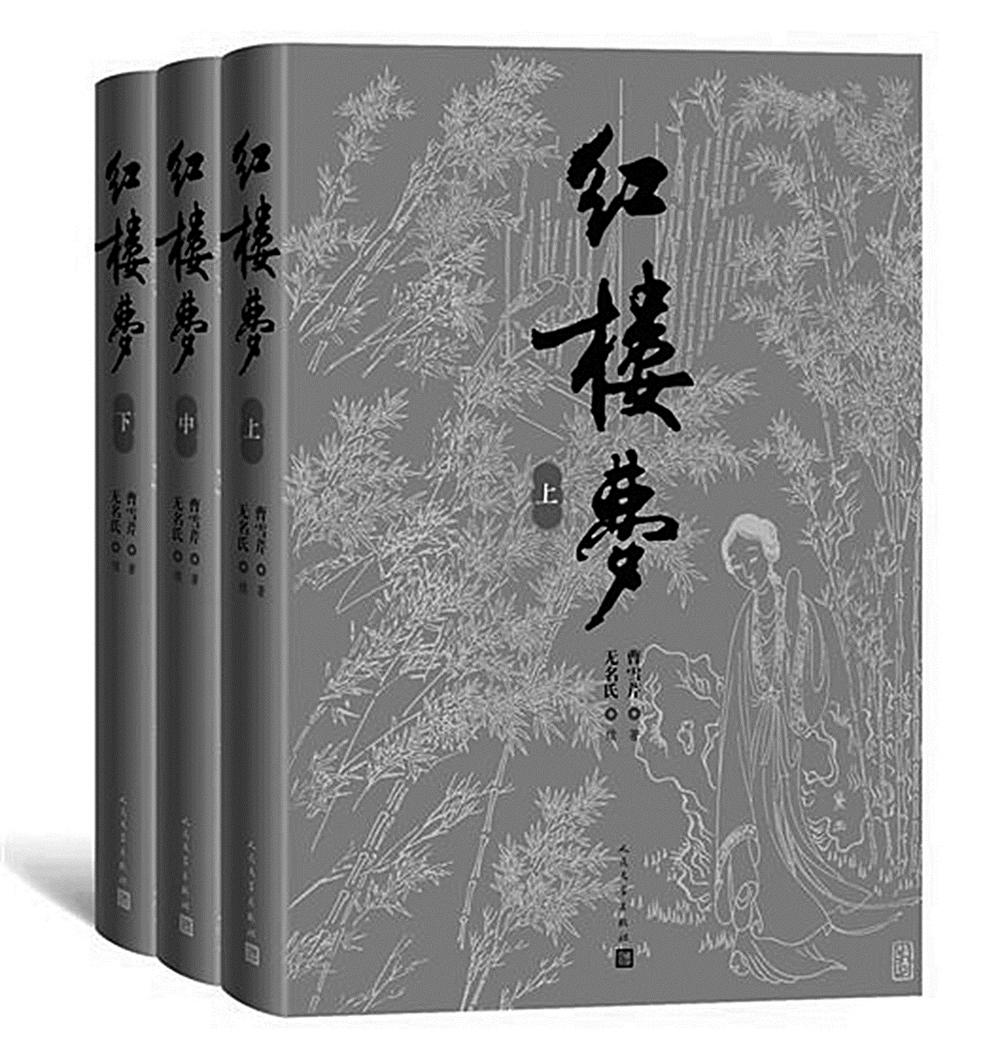□主讲人:孙伟科
主讲人简介:
孙伟科,中国红学会会长,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艺术学系主任。研究领域涉及:红楼梦研究、美学艺术学、中国现代文学等。在多种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0余篇、逾百万字。在数十所高等院校和社会单位进行学术讲座十多场,数次担任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的新闻观察员和学术顾问。著有《艺术美学导论》《〈红楼梦〉美学阐释》《红楼梦与诗性智慧》《寻真问美集——艺术长短论》等。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红楼梦》是中华文化史最伟大的著作,充满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期讲坛邀请中国红学会会长孙伟科先生讲述《红楼梦》是如何成为经典、成为中华文明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的文学瑰宝的。
《红楼梦》成为中国文学的巅峰
《红楼梦》是一部无可置疑的文学经典,在今天成为我们阅读对象中的必读物。经典之所以是经典,是因为它提出了具有普遍性的人生问题,它所提出的问题是我们一生中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家国问题、性别问题、青春价值与人生选择问题等。
然而,《红楼梦》并不是一诞生就被认为是经典。它诞生时,尚处于俗文学层次,是不登大雅之堂的。《红楼梦》作为“非传世小说”,初创时期是在志趣相投的清代宗室文人也即作者的亲人朋友之间传阅的。这就是《红楼梦》的抄本时代,几乎经历了30年的时间。直到1791年,《红楼梦》的刻印本(程伟元、高鹗作序)才开始流行。程高本出版的意义,在于结束了随抄随改、文字日见错讹的抄本时代,使《红楼梦》的文字固定下来,为它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程高本的流传,到了嘉庆年间就有了“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说法。“《石头记》一书脍炙人口,而阅者各有所得:或爱其繁华富丽;或爱其缠绵悱恻;或爱其描写口吻一一逼肖;或爱随时随地各有景象;或谓其一肚牢骚;或谓其盛衰循环,提朦觉瞶;或谓因色悟空,回头见道;或谓章法句法本诸盲左腐迁。亦见浅见深,随人所近耳。”(诸联《红楼评梦》)尽管它流行了,但并没有达到经典地位,因为在这个夸赞《红楼梦》诗句前面,还有“做阔全凭鸦片烟,何妨做鬼且神仙”的说法,和鸦片相类比,既说明它能让人爱之成瘾、欲罢不能,也说明在那个时代它有异端性和反叛性。如果《红楼梦》与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处于对抗状态,它是不可能具有经典地位的。
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红楼梦》走向经典创造了条件。先是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和口语写作,《红楼梦》作为“活文学”的代表,成为现代汉语书面与语言文字表达的首选范文和学习榜样。提出“我手写我口”走向课堂,成为新式学校教学的课本内容,这与旧学以“四书五经”为内容是截然不同的,其间可以看出深刻的社会思想的变革和时代的差异。俞平伯先生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一文提出:“红学为诨名抑含实义,有关于此书之性质。早岁流行,原不过纷纷谈论,即偶形诸笔墨固无所谓‘学’也。及清末民初,王、蔡、胡三君,俱以师儒身份大谈其《红楼梦》,一向视同小道或可观之小说遂登大雅之堂矣。”与《红楼梦》追随时代步伐走向经典相伴生的是,反对旧红学的新红学产生了。新红学以考证的方法研究《红楼梦》的作者和本子(版本)问题,使《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地位得到确认,《红楼梦》如何通过“写实”成书的面目逐渐清晰,使红学具有了现代学术的品格。尽管新红学派的大师级人物胡适、俞平伯等人对红学走向、成为世纪显学贡献巨大,但是他们对于《红楼梦》的文学价值始终不能给予充分肯定,甚至认为《红楼梦》不入近代文学之林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登堂入室,这对《红楼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们把《红楼梦》放置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来考察,走出了仅从作家个人身世、家族往事中寻找原型、素材的狭窄视域;确认《红楼梦》的现实主义艺术性质和人物形象塑造的典型性,走出了从人物形象寻找作者生平事迹和家族投影、将贾宝玉等同于作者“自叙传”的泥淖;充分肯定《红楼梦》的历史认识价值,进而确认其思想与艺术价值的空前绝后,等等。“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在《文史哲》上发表的文章,将《红楼梦》作为经典的文学价值给予了前所未有的肯定。从此,人们把《红楼梦》当作中国文学的巅峰、当作百科全书来对待。
《红楼梦》是中华民族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早在20世纪初,国学大师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红楼梦》是哲学的、宇宙的、文学的。但是以考证方法为主的新红学派却忽视了《红楼梦》的哲理价值和文史价值,使红学走上了一条只是示范一种所谓“科学方法怎样使用”的研究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方法不被学界所接受,对《红楼梦》思想与艺术的研究,才被认为是其正当的对象和范围。说起《红楼梦》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对《红楼梦》的推崇:“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文学经典《红楼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杰出代表,给了我们无比自豪的文化自信。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红楼梦》,开辟了研究新道路,红学从此走上了无比宽阔的道路。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其芳的《论红楼梦》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要代表成果,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美学与历史相结合的文学批评方法的威力和魅力。
进入思想解放的新时期以后,红学又成为引领学术对外开放的前沿。多种方法在《红楼梦》中的使用,使《红楼梦》千门万户的风景得以打开。由著名作家茅盾题写刊名、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成为学术界回归学术风气的引领者;1980年成立的中国红楼梦学会,又成为最具有群众性的社会组织。该时期,红学中的众多谜题成为全民欣赏攻关的话题,比如《红楼梦》文史互证中的“本事”谜题、《红楼梦》各抄本之间的“成书”谜题、《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是谁的“续书”谜题、如何“忠实于原著”将《红楼梦》转化为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谜题,等等。红学发展,成为我国学术历史演进的缩影。
可以说,在红学中,各种新方法几乎都演练过,各种观念也几乎都检验过。深入学习一部红学史,几乎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学术的完整风貌。由于红学的跨学科性,所以它的方法也是多样的,考证学、传记学、美学、小说学、文化学、传播学等多学科方法协同,才能推进红学的协调发展。由于红学的对象的特殊性,所以它的领域涉及文献学、版本学、曹学、脂学、探佚学等多个分支,有机组合才能再现全景地图。红学的对象是一本书、一本小说、一本《红楼梦》,但它却不是一本书的学问,也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集大成之作的《红楼梦》作为一部公认的文学经典,已经融入了我们民族的灵魂,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红楼梦》及其伴生的红楼文化,更是成为被广泛讨论和使用的文化元素,从国家外交到百姓生活,从学术研究到普及型阅读,从各组织文化活动到个体日常生活,几乎随处都能看到《红楼梦》的身影。可以说,《红楼梦》俨然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化符号。研究《红楼梦》,为的是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与繁荣,而如何创造经典,再现辉煌,走向文学高峰,《红楼梦》毋庸置疑具有伟大的借鉴意义。在《红楼梦》与文学经验的关系上,人们的焦虑也许在于:要求或希望《红楼梦》的研究者更进一步为文学经典的再创造,提供一条可以验证的规律。当代文学的焦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精品与经典的焦虑,怎样才能再造辉煌、再塑经典,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敬畏传统 弘扬经典
一部经典,不活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活在文学艺术的发展中,是称不上经典的。经典往往对后世文学具有强烈且稳固的塑造作用,可以为后世文学的发展提供土壤和武库。
《红楼梦》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中满足了不同时代的需求,也满足了新文学发展主题、题材、叙事、抒情的需求。通过父子矛盾写时代的叛逆主题,如巴金的《家》《春》《秋》;通过家庭题材写社会全景,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通过虚实相间的叙事,达到亦真亦幻的效果,如张爱玲的《小团圆》;通过强烈的文学抒情性,表达个人在时代面前的落寞、伤感、寂寥与无可奈何,如白先勇的《谪仙记》;等等。
扩大范围来讲,《红楼梦》作为文化创意之源,已经深刻地融入到了生活的各个方面。以《红楼梦》为内容的文化创意活动和文化创意产业,河北正定县的荣国府及宁荣街可谓代表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荣国府从一个影视拍摄基地出发,一路辉煌,以古典文化充实地域文化建设,以传统文化小镇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一跃成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文化旅游胜地,也成为普及《红楼梦》名著的文化基地。而今,合理地应用经典及其相关的文化遗产,丰富当今的文化建设,《红楼梦》始终率先垂范,比如建造大观园,修建曹雪芹主题公园、故居或纪念馆,弘扬红楼美食,开展红楼画展等,颇有蔚然成风之势。可以说,红楼文化繁荣与红楼火热的根本原因,在于大家对《红楼梦》的无比热爱,在于大家对《红楼梦》的无比崇敬,故而红学更要引导人们对《红楼梦》形成正确的文化观。那么,依据自己的优势和传统文化资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通过文化的再创造,古为今用,发挥创意,使曹雪芹的创造精神和《红楼梦》的文化境界、精神价值与当代文化的建设相结合,共同繁荣并不断得到发扬光大,是红楼葆有经典地位的历史责任与时代命题!
众所周知,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民族生命力、民族凝聚力和民族创造力的源泉,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建设文化强国,必须立足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汲取营养,获取力量,赋予时代精神”。《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集大成之作,作为无可置疑的经典,已经融入了我们的民族血液,反映着我们的文化心理,代表了我们民族的心声。诚如有论者所言:《红楼梦》是真正的“心理学”和现实的“价值学”,是中国人民族精神和价值精神的艺术表达。诚如斯论,《红楼梦》更深地表达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更多地反映了中国人的情感状态和行为方式。从《红楼梦》中,我们不仅可以感受它无可匹敌的艺术成就,也可以感受到它蕴含着浓烈深刻的家国情怀。
《红楼梦》杰出的文学成就和红学的丰硕成果,业已成为代表国家文化形象的一张名片。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出访中,都以《红楼梦》来展示祖国文化的软实力。早在2013年10月出访印度尼西亚的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便提到了《红楼梦》里的爪哇国。他说,几百年来,遥远浩瀚的大海没有成为两国人民交往的阻碍,反而成为连接两国人民的友好纽带。满载着两国商品和旅客的船队往来其间,互通有无,传递情谊。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对来自爪哇的奇珍异宝有着形象描述,而印度尼西亚国家博物馆则陈列了大量中国古代瓷器,这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生动例证,是对“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真实诠释。2014年3月的法国之旅,习近平总书记也曾高度赞扬旅法翻译家李治华,称他是传播中华文化的卓越榜样。99岁的旅法华人李治华历时27年,殚精竭虑翻译完成法文版《红楼梦》,成为介绍《红楼梦》到法国的第一人。习近平总书记表示,《红楼梦》是部鸿篇巨制,把它准确贴切地翻译成法文难上加难。李老的执着精神和学术才华令人钦佩。2014年10月8日,在德国法兰克福开办的书展上,十大展区7000个展位,世界各地参展者几乎都拿到了一张对开四版、由欧洲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法兰克福书展特刊。该特刊在头版整版刊发了“习近平与红楼梦、中国梦”的专题文章,同时配发了习近平总书记20世纪80年代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和30年后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首次发表“中国梦”讲话的大幅照片。中国台湾的参展人柳驷洋仔细阅读后评价道:“习近平先生29岁谈红楼梦,59岁说中国梦。这样有梦想的政治家,难得!”法兰克福书展媒体中心在开展首日上午,也把这条新闻在官方Twitter播发。2015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访美期间向塔科马市林肯中学赠送了《红楼梦》《白话史记》《唐诗》《宋词》等中国古典作品。可以说,《红楼梦》当之无愧地传达和培育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的“红楼”外交,显示出《红楼梦》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武器,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以文学名著《红楼梦》为渠道的这种灵活的外交策略,从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角度开掘出了中国梦崭新的世界性人文深度,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精神志气,提振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提升了中国在世界上的话语权。
《红楼梦》是经典,我们敬畏传统与经典,但我们对待经典的态度,不应该是神化它、膜拜它,而是应该向曹雪芹学习。学习《红楼梦》“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打破了”的创新精神,学习曹雪芹以诗性文本展开对话的平等精神和人文精神。执着还是解脱,故乡还是他乡,有为还是无为……在这样的终极追问中自我深化与不断升华,以学术求真,以文学求善,以艺术求美,让真善美相统一的无限追求成为焕发文化创造力的根本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