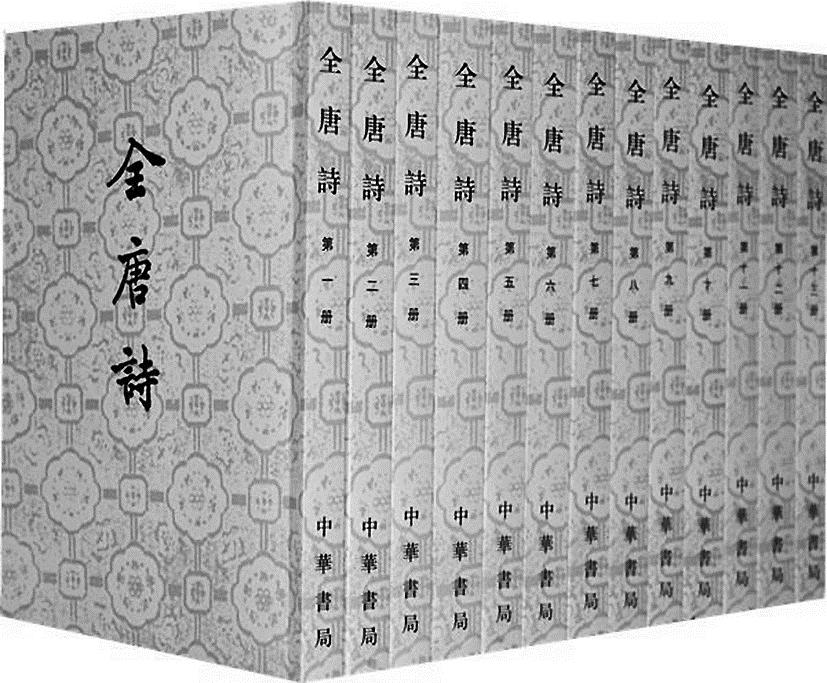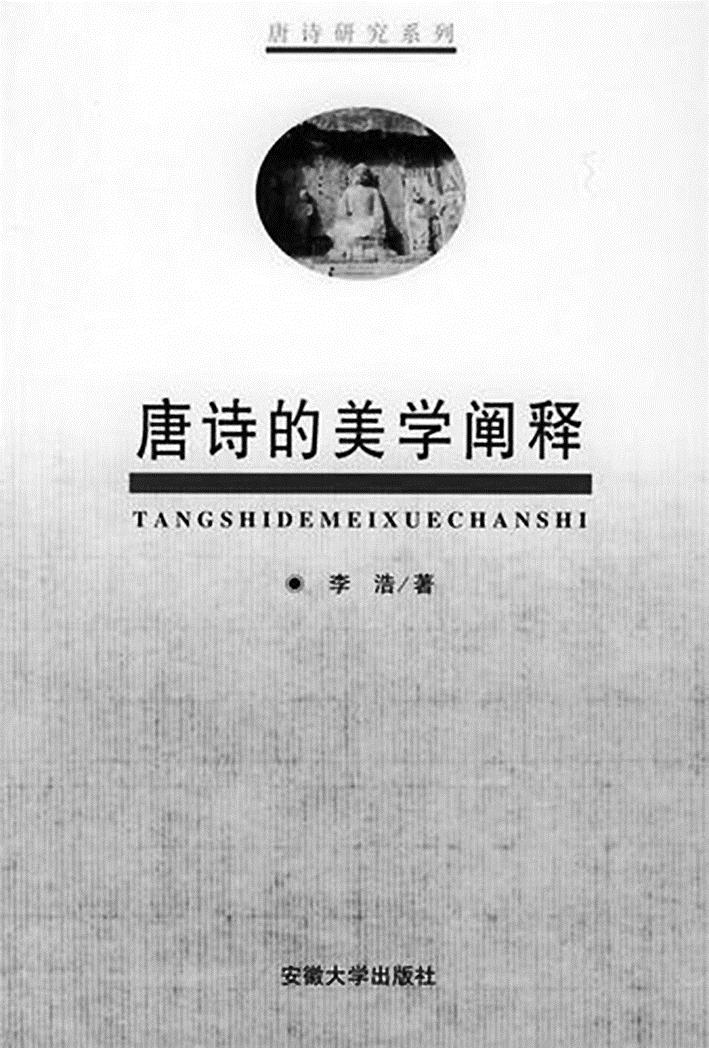□主讲人:李浩
主讲人简介:
李浩,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西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兼职有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长等。著有《唐诗的文本阐释》《唐代关中士族与文学》《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究》《摩石录》《濡羽编》等学术著作。教学科研成果曾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等。
编者的话:
唐诗是唐代的一种文学形式。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曾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来说明中国文学史上每一个时期的文学各有所长。唐诗代表着唐代文学形式的最高成就。“文化精神”的含义是指作为本质要素和内在命脉的文化传统,是一种文化特有的价值观念系统,亦即一种文化哲学。这是文化中充满生命活力的具有原初性和本根性的基质。唐诗与文化精神,可以狭义地理解为唐诗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精神,也可以宽泛地理解为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联性。本期讲坛内容取后者之意。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从历史的或时间的角度去理解,也可以从逻辑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与逻辑并重是历史研究的基本路径。本期讲坛邀请李浩教授从这两个视角来介绍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即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和理论含义。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
从时间演变的角度看,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打破传统到建立范式
唐诗所产生的时代是一个全新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包括唐诗的形式,都是全新的。
唐诗开始于对传统诗歌的批判。以陈子昂和李白为例,陈子昂就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对六朝诗歌和初唐诗歌进行了大力批判,而李白也在《古风》等诗歌中对前代文学进行了批判。
唐诗包括古体诗和今体诗(近体诗)两种。古体诗在唐以前就已发展得比较成熟了。唐人也写古体,如陈子昂的《感遇》、李白的《古风》《蜀道难》《将进酒》《梁甫吟》等都属于古体诗。今体诗则是在唐代才逐渐成熟并定型的诗歌形式,即律诗和绝句。律诗又分五言律诗和七言律诗,绝句又有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和六言绝句。这些都是在唐代定型的。
“不破不立”,唐诗打破了旧的传统,创立了新的范式。这种新的范式、新的权威,一方面可供后人学习继承,另一方面也为后人提供了可借鉴的对象。
从雅到俗的走向
唐诗的趣味主要是雅的趣味,这种典雅、高雅的趣味来源于南方文学,而北方地区的作者对这种南方风气非常迷恋,成为热情的模仿者。于是南方文学趣味风行天下,唐代宫廷君臣都弥漫在这种典雅中。
隋唐以前,中国曾经历了300多年的动乱时期。继西晋之后的东晋已将都城迁到了南方的建康,南方地区在东晋以后又经历了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地区被少数民族政权占据,杨隋政权虽然在政治上否定了北周,但在文化传承、家族血缘上却与前代一脉相承。
东晋以后,中原文化整体迁徙到了南方。王、谢等大家族原来都是西晋的王公贵族,“永嘉之乱”后,举家迁徙到南方,把整个大家族迁至建康,也把中原地区的高等级文化整体带到了南方,迅速提升了南方地区的文化水平。
中国文化发展之初是北方文化高于南方文化的,但历史上的三次大迁徙改变了这一局面。因此,陕西或曰西北乃至整个北方整体落后于南方在北宋之后即已形成。一个简单的事例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点。宋以后的科举状元主要出于南方地区,元明清几百年间也都如此。有时南方一省所出的进士、举人人数即超过了整个北方多个省的总和,如江苏、浙江、安徽等,都是如此。
隋至唐初,南方文化是正统,文人的趣味也好尚高雅。因此当时北方文人喜学南人。隋统一战争中,除了在取建康时有过一些军事冲突以外,占领广大南方地区时,几乎没有大的军事战争。杨广到南方后,说吴语,唱吴音,用南人为智囊,并与南方贵族萧氏联姻,从而受到南方贵族的欢迎,也使南方免于战火。唐太宗本是个胡汉混血的西北汉子,却很喜欢南方柔媚的宫廷诗,书法则好南人王羲之华美流丽的行草而不喜北方强劲朴拙的魏碑,并曾想方设法地谋取《兰亭序》。
唐代文学在初期也是南方的雅文化趣味,而在发展过程中则逐渐由雅变俗,从宫廷走向江山塞漠与街坊市井,至中唐出现了白居易的俚俗之作,其诗“老妪能解”。可以说,唐诗发展经历了一个由雅而俗的变化。
从文体看,这种由雅到俗的转变也是很明显的。诗这种文体还是相当典雅的,后来出现的词,尤其是早期词作,是颇近俚俗的。唐代传奇也是比较典雅的文体,是文人的作品,也表现出文人趣味。而发展到宋代的话本小说,其俗意就很重了,传达出浓厚的市井趣味。后者即使今日之一般读者,也很容易看懂,而读懂前者就需要相当的素养和训练,尤其《游仙窟》之类的传奇。骈体文也是一种雅文体,而后来日益盛行的散体文就相对通俗了。
从贵族传统到平民气质的走向
唐的前身是魏晋南北朝。著名唐史专家陈寅恪先生曾指出,唐代文化有两个来源:一是西魏北周的文化传统,一是南朝齐梁文化传统。
齐梁文化即是一种贵族文化。许多历史学家都曾提及门阀士族、门阀制度的问题。严格意义上的门阀制度应该说只存在于东晋时期(参见田余庆《东晋门阀士族》一书的相关论述),而广义的贵族文化却存在于自东汉经魏晋南北朝而至唐代这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在这个问题上,内地的史学教科书与海外汉学界存在着很大差别。内地学者多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一个贵族时代,而唐代打破了这种局面,是一个平民寒庶在社会各领域地位充分提升的时代。海外学界提出,贵族制度的结束当在北宋与南宋之交,因有“唐宋变革论”之说,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就是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到北宋末期彻底崩溃,此后便进入了官僚社会。贵族为世袭,官僚授职则要看子弟个人素质。同时,魏晋至隋唐有一些大家士族,其传承绵延数代,脉络清晰。唐末五代至两宋之交的几次大动乱,使这些士族大家彻底解体,几代同堂的大家族变成了与近代接近的所谓“核心家庭”。
北方文化是胡汉贵族文化的交融。北魏孝文帝改革中,反对鲜卑贵族间小圈子内的通婚,鼓励入主中原的北魏鲜卑军事贵族同洛阳附近的中原汉族贵族通婚,即同崔、卢、李、郑、王五大姓的贵族通婚,打破了胡族小圈子内的贵族通婚,形成了胡汉融合的大贵族圈子。
隋唐统治者实为关陇贵族,是关中贵族与鲜卑等其他少数民族贵族的结合,实质也秉承着一种贵族传统。这种贵族传统入唐后受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冲击,变得不那么纯粹了,成了一种较为松散且不断受到破坏的传统,并逐渐走向了解体。
古汉语是一种非常典雅的语言。同样的意思,用文言和白话表达就很不一样。这种高雅只有在古老的语言中才能储存。
正因为如此,中国文学作品特别是如唐诗这样的作品就很难翻译。司空曙写给卢纶的诗中有“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句子,他并没有说久别重逢的激动心情,只是出现了一些自然意象。李白赠友人诗中亦有“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句子,如果要用典范的英文翻译,“落日”与“故人情”的关系就成了个大难题:落日是故人情,似故人情,还是代表故人情?汉语的含蓄使诗意耐人咀嚼,也不宜被翻译。伟大的作品是“抗译”的,这正是唐诗文化的独特魅力。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论含义
从共时的、逻辑的层面看,唐诗中蕴含着中国文化精神的丰富内容。
唐诗与中国文化的
原始创新精神
第一,诗体的独创。唐诗包括古体诗和今体诗,其中今体诗又称格律诗、近体诗,为唐人新创,影响了此后长达千年的中国诗歌。今人写诗仍是按唐诗格律来写的。这种诗体在篇章、句式、对偶、音律等多个方面都有严格限定,同时亦具有音乐声律、语言修辞等多种形式美感。今体诗包括律诗和绝句两大类。就字数而言,可分为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此外还有作品极少的所谓“六言律”。“诗圣”杜甫即是格律诗高手,代表作有《秋兴八首》等。今人不论创作诗歌还是评论诗歌都是以唐诗为范本的,可见其影响深远。
第二,诗法的独创。唐诗的独创在技法上表现为对仗中的流水对、扇面对以及拗救、通感等多种手法的灵活运用。
对仗古来有之,但流水对、扇面对却是唐诗新创。流水对是指上下句有前后相承关系,同时又彼此对仗,如杜甫的“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扇面对,又称隔句对,是指具有对偶关系的上下四个句子,第一句与第三句、第二句与第四句分别相对,形同扇面。拗救,是指上句不符合格律,下句补救。杜甫最善此道,后代的苏轼、黄庭坚及江西诗派都专学这一路。通感是一种比较特殊的修辞方式,为了造成特异的美感,将视、听、味、触等多种感觉互相打通,互相挪用。如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描摹琵琶音乐的大量诗句:“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调动了种种想象,将听觉比喻成各种感官的感受(详见拙著《唐诗美学精读》第三章的相关论述)。
第三,诗境的独创。境界是中国古代诗论的重要范畴,也是对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审美规定。行家评诗多用专业术语,称“有境界”“有意味”。唐人不仅奠定了境界理论的基本原理,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创作了许多境界浑融、气象高妙、神韵悠然的杰作,成为后世作家不可企及的范本,可以说境界最能体现唐诗的艺术特征。简而言之,唐诗追求的境界是源于形象而又超越形象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代表性的人物如王维,有《辋川集》二十首,其中《鹿柴》一诗很有代表性:“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
众人皆知王维诗中有画,不知其诗中有佛、诗中有禅。他的诗境空灵,颇有禅宗的高远境界。近代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强调诗词要有境界,并将境界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无我之境”即是空灵之境。
王维诗在后代很受尊崇,清初王渔洋及其“神韵派”就标举王维诗中的神韵。宋人严羽在其《沧浪诗话》中曾说,好诗应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也应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诗中的体现。
第四,诗用的独创。诗在唐朝可谓无所不能。唐代士人如欲进入政府部门,必须经过科举考试,第一场是帖经,考儒家经典的记忆背诵;第二场为杂文,考诗歌、辞赋写作;第三场是策论,考应用文写作,对社会现实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因此,诗艺高低与政治升迁、仕途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人说唐代因文学的繁盛而抑制了科学的发展。是耶非耶,姑且不论,但唐代文学的发达确实造成了一种泛文学、泛文化的现象。
唐诗与中国文化的
开明开放精神
中国文化是一种尚文而非尚武的文化。对一个地区的统治讲究人文化成,以文教德化使边远地区感动归顺,而不是武力征伐。《周易》中有“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语。《论语》中提出:“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正是孔子的治国理念。
唐诗中不仅可以看到汉族文化,也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文化,更能见出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频繁交流。
白居易的诗歌通俗易解,唐宣宗在白居易去世后写诗追记其诗歌流行状况时提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说明其诗歌普及流行之广泛,堪称当时的第一畅销作家。白居易的诗歌还广泛流传至周边的日本、朝鲜(时称鸡林国)。当时来华商人在经商的同时,热衷收购白居易的新诗,且能识别出真假来。白居易在日本影响很大,《源氏物语》中引用了多首白居易的诗歌。
与此同时,外国的风尚习俗也大量流入中国。中唐后流行的曲子词,其中的一个词牌“菩萨蛮”,就是自印度、斯里兰卡、缅甸等地传入的。唐代音乐分两部分:一为雅乐,是宫廷的祭祀音乐;一为燕乐,是日常生活庆典等使用的音乐,其中又有“九部乐”“七部乐”等。唐乐中大量引用西域、南亚、中亚等地区的音乐,有的是原封不动地保留。正如鲁迅所言,唐人胆子很大,对外来文化敢于釆用“拿来主义”态度。这充分说明唐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心理也很健康。当然也有个别废止的,如“泼寒胡戏”,即是当时西域的泼水节风俗,盛唐时传入长安,大臣贵族颇多非议,后遭禁止。总体而言,唐代对外来文化的态度非常开明。
唐代与外来文化的交流可以说无处不在。西北大学曾发现一方唐代日本来华留学生井真成的墓碑,记述他学于唐、仕于唐、病逝于唐的一生。这一发现在日本引起重视。一个外国人可以在唐政府中做官,于此也可见唐代开放的力度之大。唐时在长安居住的外国人很多,有一些人还通过科举进入唐政府机构任职,如日本的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韩国的崔致远等。日、韩等国的有志青年很多都来唐参加科举考试,对唐科举的重视程度一如当今国人取得高等级学位一般。唐代科举中曾专为外国人开“宾贡”一科,考中者可留唐任职,也可回国。
唐诗与中国文化的
尚文尚雅精神
今人尊孔子为儒家开创者,视山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实质上,儒家思想文化的来源是陕西关中。孔子非常推崇周代的周公以及西周文化,其思想来源多出自周代的礼乐文化。《论语·八佾》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标明了孔子尚文的思想渊源。孔子“克己复礼”的“礼”也就是周公所定的文化准则。西周的礼乐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尚文尚雅的传统。
唐诗挖掘了汉语的诗性潜能,把汉语的美推到了极致。今日社会使用现代汉语,唐诗用的是古代汉语。古代汉语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中古汉语,包括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其代表为唐诗宋词,语音以长安音、洛阳音为基本音。迁徙流动造成了文化的南移,也造成了语言文化和语音的南移。中古时操长安音和洛阳音的人群随着战乱,已经整体地大规模地成系统地南迁,他们的这种口音为南人所模仿。今日的广东、福建等地方言如客家话等,保留了很多中古音。
中古汉语的特点是高度浓缩、高度概括,因此诗歌特别凝练。杜甫《登高》中有“风急天高猿啸哀”句,短短七字中含有三个主谓结构。后句“渚清沙白鸟飞回”亦是如此。有的诗句,只是一系列名词的并列,没有主谓结构,也没有动词,如“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是杜甫思念李白的诗句,他并未描述如何思念,只是排列出一系列意象,但是诗意已尽在意象当中,将汉语诗的特点推到极致。汉语是最适合写诗的语言之一。
唐诗与中国文化的
崇尚自然精神
唐诗与中国文化崇尚自然的传统有两层含义。
首先,唐代诗人喜爱大自然。唐代有大量的山水诗、田园诗。唐诗中最好的句子不是直接表达感情的,而是用自然意象写成的。如“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都是以自然意象胜。
其次,唐人在精神上追求自然、返归自然。唐代诗人充满进取精神,如李白、李商隐等都将其人生的理想模式设定为先入仕实现政治抱负,辅佐皇帝建功立业,功成后则归隐田园,回归自然,享受山水安逸之乐。《安定城楼》是李商隐年轻时抒发抱负之作,“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即用《吴越春秋》中范蠡的典故。范蠡先是帮助勾践灭吴复国,功成之后携西施归隐五湖,成为富甲天下的陶朱公。这是唐代许多诗人理想的人生模式,李白诗中也表达出类似的想法。从这种理想的人生模式中也可看出诗人内心回归自然的想法。
唐诗与中国文化
追求雄大刚健的传统
唐诗崇尚大气,崇尚阳刚之美和雄浑壮阔的风格,与宋词以婉约为美截然不同。初唐陈子昂追求“汉魏风骨”,杜甫诗以“沉郁顿挫”胜,盛唐诗歌中一直洋溢着进取雄健的精神。唐诗虽然深受南方文化影响,但主旋律仍是北方文化的大气雄浑,这与入主朝廷的主要是西北人有关。唐代统治者来源于西北胡汉杂处地区,崇尚雄大的气魄。唐诗有悲怆感,却没有绝望感。陈子昂的小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其中有悲伤,有孤独,也让人感受到人的渺小,给人以悲剧感却并无绝望。悲剧也是阳刚之美,这正是唐诗雄健刚劲精神的充分体现。
唐诗与中国文化的
和而不同精神
儒家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同”“和”最早都是音乐术语。“同”指单音的重复,“和”则是一组旋律有规律、有特点的变化:出现、展开、再现、高潮、结束。“和”是由不同声音的配合而构成的。
大唐之音,是和而不同的。唐代并非儒家一家之天下,而是儒、释、道三教并存的。终唐一代,皇帝们对佛教的态度还是非常开明的,佛教得以自由发展,且流派众多。除了佛教,唐代道教及中亚地区的一些宗教如景教、摩尼教、祆教等,也都在唐代有很大的市场。
唐代也是各种地域文化并存的时代。作为统治基础的关陇文化以及江南文化、山东文化和少数民族的草原文化都是共生并存的。
不同种族的文化也在唐代并存。唐史研究者很多都关注过“胡将”这一特殊现象。唐政府广泛任用胡人为国家的军事指挥员,如安禄山,另如史思明、哥舒翰等也是玄宗时重兵在握的胡将。有统计说唐代大、小胡将有几百人之多。文臣可用外国人,关涉国家安全的武将也能用外族人,唐代统治者的心胸气魄,令人感叹。
唐代也是不同阶层文化并存的时代。唐代虽是贵族社会,但已经到了贵族社会的后期,不是完整的贵族社会。各阶层人群的利益都在制度中得到体现,也都有自己的影响。唐代诗人来自不同阶层,因此唐诗也是不同阶层、不同等级、不同地区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发出的不同声音,傅璇琮先生曾借用泰纳《艺术哲学》的一个比喻,说唐诗是由不同声部构成的一曲恢宏的大合唱,而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则是不同乐段上的天才领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