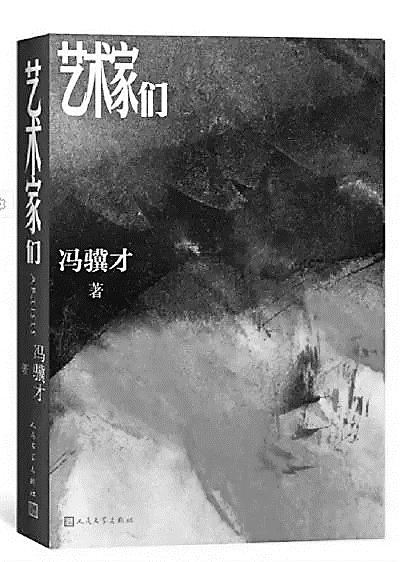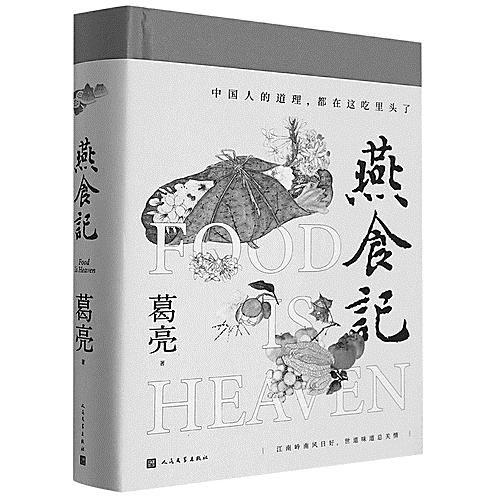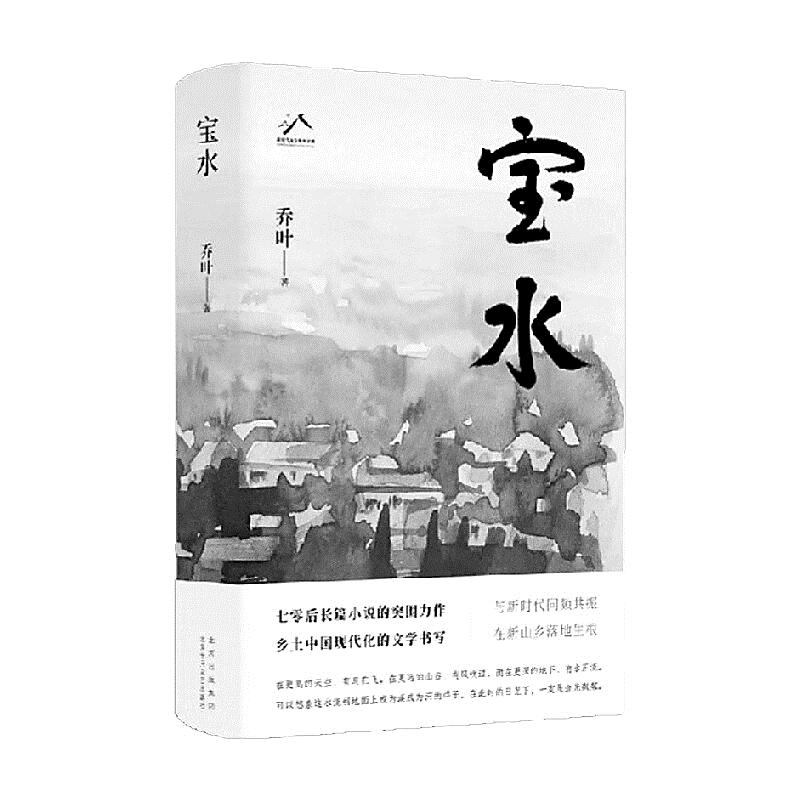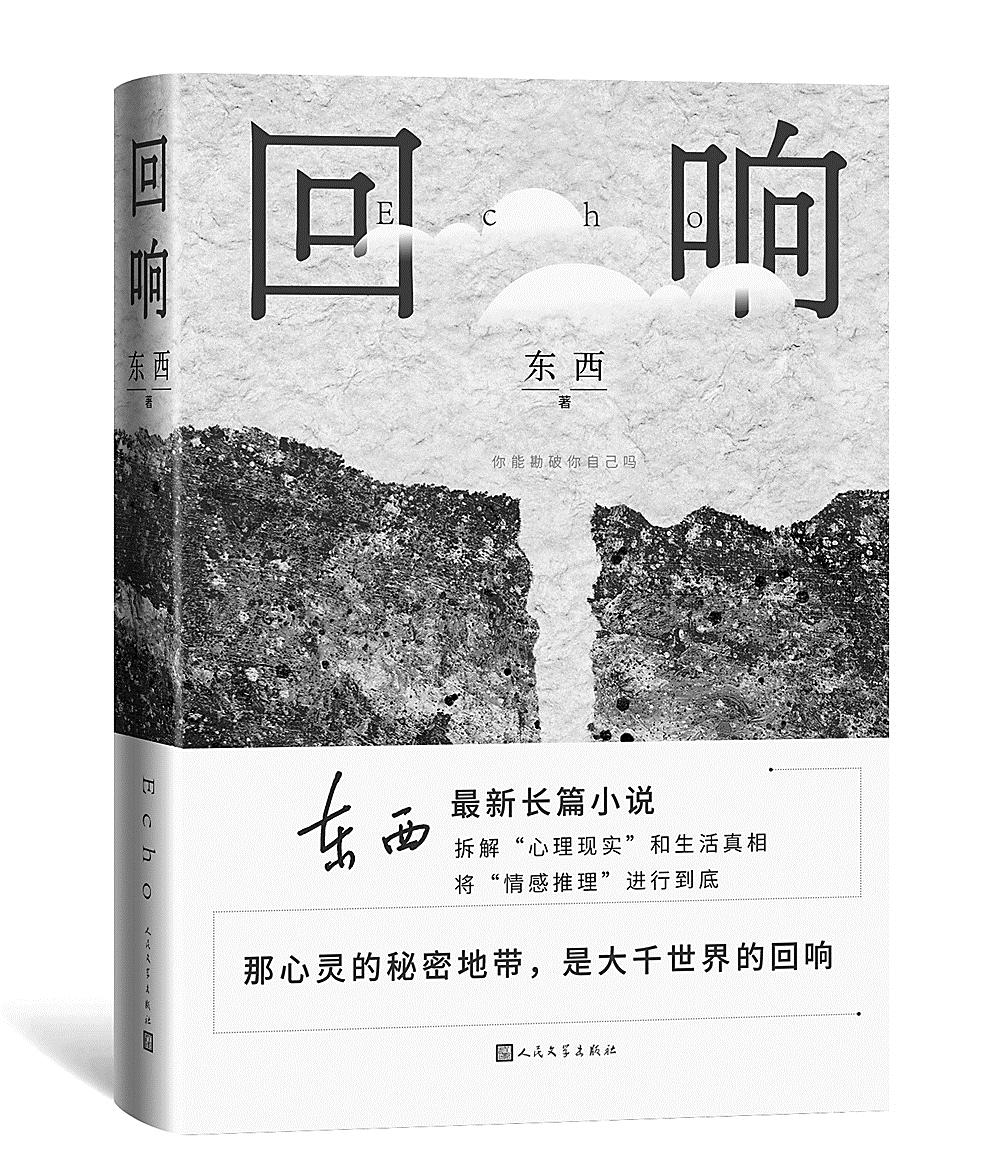主讲人简介:
李掖平,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东大学东方诗学高等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先后出版学术专著、合著10多部,发表文学研究和影视评论文章500余篇。主持国家级、省部级社科研究项目多项。曾获山东省优秀教师、山东省师德标兵、山东省教学名师、山东省优秀研究生导师等多项荣誉称号。
编者的话:
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七个着力”的重大要求,其中强调“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等。当下文坛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可谓热潮澎湃,尤其是长篇小说更是佳作迭出,牵引着广大读者的阅读聚焦和评论者的诠释解读。李掖平教授对2020年以来5部优秀长篇小说(冯骥才的《艺术家们》、水运宪的《戴花》、葛亮的《燕食记》、乔叶的《宝水》和东西的《回响》)的阅读与解析,讲述新时代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
讴歌真善美的主题建构
冯骥才先生的长篇小说《艺术家们》,于2020年10月出版。小说讲述了一群艺术家主要是三位画家,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到新世纪以来从初心一致到结局迥异的生活故事。
小说主人公楚云天、洛夫、罗潜都是年轻画家,号称“三剑客”。他们在荒诞年代里默默守护着共同的艺术沙龙,从唐山大地震中幸存下来又一起迎来了改革开放。但当精神解禁、生活渐好,三人却从志同道合逐渐走向了分道扬镳。洛夫被商业化浪潮吞噬,失去了本真,最后自杀;罗潜苦苦挣扎于社会底层,耗尽了绘画才能;只有楚云天最终守住了对艺术的赤子之心。作者在小说前言里说:“我一直想用两支笔写这本小说,我的话并非故弄玄虚。这两支笔,一支是钢笔,一支是画笔。我想用钢笔来写一群画家非凡的追求与迥然不同的命运;我想用画笔来写唯画家们才具有的感知。”作者以这两种笔调的融汇或者说杂糅,一方面理直气壮地讴歌真善美,另一方面旗帜鲜明地鞭挞假恶丑。作为与书中“三剑客”同时代的作者,“大冯”深知他们的所思所想及苦乐何来,“是在哪里攀向崇山峻岭,是在哪里跌入时代黑洞,又是在哪里陷入迷茫,以及他们调色盘中的思想与人性的分量”。因此,当描写三位画家在几十年间关乎个人命运和个人情感经历的种种故事时,主题指向始终紧扣其灵魂的挣扎沉浮和人性的向真向善向美。不仅写出了画家们在善与恶、好与坏、混沌与清晰、复杂与简单之间是怎样模糊了界限,消弭了区别的人性悲剧,又写出了身陷泥淖之中他们如何警醒鞭策自己,必须保持一种审美独立性,必须与世俗拉开距离的那种艰难困厄。作者对于商品时代物欲横流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三剑客”都曾被名利追逐的揭示。洛夫是被经济利益追逐,楚云天是被声名欲求驱使,罗潜则是被趋俗世道挤压。作者坚守“艺术家是永远不可能和世俗融为一体”的审美立场,以饱满的激情,或借用人物之口,或转述他人话语,或直截了当评议,对这三位画家的不同经历和命运进行了层层深入的辨析,字里行间流溢出剖析、思辨、批判、褒扬缠绕为一体的真情实感,能指着“真正的艺术家不管什么时候,都绝不能放弃对真善美的追求,同时也绝不能放弃对恶与俗的鞭挞,绝不能放弃对黑暗的挑战与抗争”的精神气质。这不仅是一位优秀作家的风骨、气质和内在修为,更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气、神。
水运宪的长篇小说《戴花》,首次出版于2022年10月。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工人莫正强竭尽一生全力以赴争当劳模的故事。作者秉持现实主义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立足价值引领的正能性、审美能指的多重性、阅读接受的生动性的三位一体,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砥砺前行搏击进取的现实律动,以历史视域、社会角度、个人生命体验的错综交织,以正德大义的庄重言说与雅俗共赏的生动表达的有机结合,以故事的丰富思想蕴含、事件场景的鲜活形状与色彩、人物形象明亮的人格光束和接地气有活力的鲜明个性兼具强烈情感认同感染性与共情力的语言表达的互融互衬,谱写出一曲中国机械工业不断走向强盛的时代壮歌。小说聚焦某高校机械制造专业的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德华电机制造总厂参加工作的历史事件,多视角、多维度、多样态地描绘再现了1960、1970年代作为共和国主人的基层普通工人,任劳任怨干工作、争先恐后当劳模、孜孜以求钻研技术革新的曲折历程,从中国电机制造工业技术革新的一个侧面,钩沉出中华民族在困厄中破旧立新、求变图强、砥砺拼搏的历史发展逻辑,进而构建起一个兼具广度、力度和深度的宏大主题。“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唱歌要唱跃进歌,听话要听党的话”,作为主人公莫正强最喜爱的这首歌,既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表征,又是人性尊严的光荣归属。由此,《戴花》将潜藏在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中的中华民族“英雄情结”的历史基因、文化血统和蓬勃向上的当代精神生动可信地呈现出来,深刻揭示反映了中国工业强劲发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以引领社会生活和人心人性的“明德”风尚。
葛亮的《燕食记》以香港著名的岭南风味美食为中心,在从20世纪初至今近百年风云际会的时代背景下,描摹写生香港社会和各色人等与美食相关联的日常生活,笔力的重点始终放在呈现民众俗世的现实日常生活,及其或热闹或寂寥或浮华或沉潜的世态人情,只为记存那相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和宏大社会主题而言,更为生动具实、更为丰富鲜活、亦更为真实可信的时代光影和生命存在。然而,如实描摹不禁使人眼前一亮食欲大动、更使人艳羡不已心向往之的香港和岭南美食小吃的各色样态,绝非葛亮的终极艺术目标。写一部关于饮食的小说,只是他的一个创作计划,通过多角度多侧面地呈现和敞开弥散在整部小说书写空间里,充盈在岭南普通民间日常生活里,沉潜在各色美食小吃的制作技艺里,鲜活在众多人物形象性格里的诸如悯恤、疼惜、从容、节制、洁净、崇德、尚爱、向美等传统文化因子的丰富蕴藏,为深蕴岭南美食中的中国人特有的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绘态画魂,借此廓清和厘定传统文化精髓对中华民族性格的根性支撑,借此敞开并礼敬香港乃至中华大地上一切“人格之德”的美丽与魅力,才是葛亮之所以要写这部小说,而且将其写到了一个清晰可见的高度与深度的创作旨归。这种别开生面的书写方式和审美效果,彰显出的恰恰是作者对历史和文化、对社会和人性、对生命和生存、对写实和抒情的独特理解和认知。
乔叶的《宝水》,获得了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其主题是为新时代乡村绘态画魂。作者满怀对故土和乡民的深情,以一种“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的悯恤情怀,秉持着对乡土文化与农民根性的细致而深刻的观察与个人思考,将笔触深入到乡土社会的法礼德道、人伦亲情的血缘地缘、乡村经济新格局的系统构建,以及土生土长本村人和形形色色外来客的生活百态等各个方面,有机融汇起深厚的历史感、宽阔的命运感和向善向美的引领力。这种历史深度、命运厚度和引领力的高度,不是建立在对农村经济发展变革重大事件的宏观描写之上,作者巧妙地选用了一种以小见大举重若轻的艺术处理方式,将文学书写的聚焦点或者说追光点放在了一个小小的宝水村,通过对宝水村从推出美丽乡村的自然景观,到建立乡村旅游的农家乐体系,再到系列农副产品的文创开发和传媒推介的一步步发展提升等诸多日常性、具体性、普遍性三位一体的乡间小事、普通农人、寻常过往的描写叙述,建构完成了为新时代中国的乡村振兴立根,为良善而时有狡黠、坚忍而坚韧的乡土众生立命,为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心一意奔小康的广大农民立心的重大主题。
东西的《回响》,也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本部小说的题材属于缉凶惩恶的刑侦推理范畴。作品通过对一个颇具戏剧化和极端性的案例,剑走偏锋式地展开了对当代人隐秘而复杂的情感与心理纠结,步步深入、层层剖开、探幽发微且不厌其详地追溯和探寻,成为当下文坛上收获“如潮好评”的一个瞩目热点。主人公冉咚咚是一位女警官,在侦破一桩名为“大坑案”的凶案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丈夫在宾馆私自开房的记录。于是,冉警官既要侦破案件,又要像侦破案件一样侦破丈夫为何开房,开房后究竟干了些什么,两条线索的心理较量由此同时展开。冉警官具有高超出众的侦探能力,透过重重迷雾抓住些许可疑的蛛丝马迹,层层深入剖析,最终使夏冰清的命案告破;但她揪住丈夫开房一事不放并步步紧逼层层深挖,从伪装层挖到真实层再挖到创痛层,已让丈夫几近崩溃,最终导致了婚姻破裂家庭解体。由此冉咚咚开始反思自己,心中升起了对丈夫的深切愧疚。作者借助推理小说的外表,对当代社会生活中的社会心理、个体心理,以及个体心理最隐秘的无意识、犯罪心理,精神抑郁症等问题,都做了特别深入、特别广泛地挖掘和探究,继而从个体伦理中存在的荒诞、虚无等空隙处入手,发出对个体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究竟是什么的哲理追问。
精妙的叙事结构和表现形式
《艺术家们》主要是扣住三个画家的绘画奋斗史,沿着其家庭生活、感情波折等线索进行纵向书写的,这种单纯的线性结构,往好处说是高度聚焦,往危险处说就是生活面看上去相对狭窄,因为里面大量关于音乐和绘画的描述是一般人较难产生共鸣的。不懂音乐绘画的人,不是纯文学的爱好者,较难读下去。但真正懂文学懂艺术爱小说的读者则是看一眼就难以搁置,因为作者将丰富的社会生活和人性纠结全都打散后,有机交融化合在这三位画家对绘画和音乐的痴迷执着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感情婚姻生活)中。三人感情经历的描写分别以三种叙事方式展开——由假借他人故事的转述、周围人各个角度的反映的碎片拼接、正面描写刻画这三种方式搭配而成。罗潜的感情经历是借用他所转述别人的故事浮出水面的;洛夫的感情和婚姻是用别人为他担忧的眼光一次次看过去、一次次惋惜性的背后议论碎片式拼贴出来的;楚云天作为“三剑客”的中心人物,另外两个人的故事都由他勾连起来,所以其情感纠结一直都是正面推进的。这三人情感和命运互为呼应又互为参照的跌宕起伏,既共性地折射着时代光影,又个性地契合着人性的内在肌理,有效激活引发了读者的共情。
《戴花》构建起的是一种由一条主线勾连起多条副线的拧绳式框架结构。叙述主线始终沿着“我”(杨哲民)和师傅莫正强之间的工作、生活,以及师徒关系的叙述路向,具实严谨地顺序推进莫师傅孜孜以求争当劳模的故事讲述;而包括“我”和同学们的友情、“我”和姜红梅的爱情、同学们之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吴启军和他的师傅段一村的师徒关系、师傅莫正强的家庭生活,以及师傅与许多人的或交好或纠结或误解或抵触的复杂关系等多条叙述副线,则沿着花开数朵、各表一枝的轨迹,以或顺序、或倒叙、或插叙、或碎片拼贴的方式向前铺衍。这种多线索多角度多层次多样性此起彼伏的交叉描写,始终紧扣各种矛盾冲突、紧贴人性的善恶纠结有条不紊地展开,既强化了小说文本杂树生花起伏跌宕的故事性,又敞开了前有伏笔、后有照应的可读性和感染力。情节的推进并不过多依靠翻天覆地大起大落的陡转,却以生活、生产、爱情等日常细节的细腻刻画,成功搭建起一条物质性的“叙事本文”与内在精神性的“心理本文”交相辉映的阅读渠道,有效触发了读者因真实生动而可亲可信而心生敬意的同频呼应。事件和场景的描述具有鲜明的画面感,人物对话既能指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洋溢着鲜活的日常生活气息,亦写照着朴素遒劲外简内丰的古典神韵。这种具有鲜明现实指向性与写真纪实意义的描写和刻画,滤掉了一切粗简的直白和浮夸的修饰,剔除了影响文学性的所有泥沙,既真实可信又很接地气,使读者真切而深切感受到德华电机厂这片文学“风景”中的灵魂跃动与人性交响,标识出作者巧妙叙事策略和纯粹白描手法背后的深厚文学功力。
《燕食记》精妙设置了互融互衬的三重叙事复调:一是非虚构书写与虚构书写的叙事复调;二是人物形象与美食技艺的格物(人品与物格)复调;三是历史(过往)与现实(当下)的对话复调。非虚构书写与虚构书写的交织缠绕和融通关联,构成了《燕食记》的第一重叙事复调。小说是以一种故事中的主人公与创作主体(作者)进行平等对话的方式来构建和完成叙事的。非虚构书写主要落实对故事中主人公生活经历和情感旨归的那些写实性叙述描摹层面,而虚构书写主要践行于创作主体作者对故事中人物经历的那些时空的浪漫性想象联想层面;女性形象的精神气质与各色美食的物格之间的互文性,构成了《燕食记》的第二重叙事复调,即人品与物格的复调。第三重历史(过往)与现实(当下)的对话复调,则是经由以“出虚入实,虚实相生”的故事叙述方式得以建构的。虽然故事的讲述是由“我”要完成关于粤港传统文化口述史的研究项目而拉开了帷幕,但故事正式进入讲述环节,则是“我”找到了故事的主角荣贻生(小名唤作阿响)后的系列亲身经历和所感所受。追溯和还原历史上某些事件留下的印痕,对“我”来说是一份为了寻绎和确证一个伸向无意识深处的标尺,或者说是为实现对历史记忆的一种现代编码和当下定型的工作。因此这种追溯和描摹,就可以名正言顺而且理所当然地放飞艺术想象力和联想力,任由其衍生出无限广阔、无限丰饶、无限具实又无限浪漫的细节,建构起一个足够安放风云际会的社会背景、环环相扣的矛盾冲突、杂树生花式的人际关系、广阔深密的心理意识流动的文学空间。毫无疑问,它既是虚的又是实的。其“虚”,是指在创作主体的想象力和联想力的推进延绵中,所有的过往时空都可以沿着或再现或扭曲或畸变的路向重新构建。其“实”,则是指创作主体的所有思绪毕竟都牵系在创作主体“在当下现场”的亲身经历之中。当互不相容的各种独立意识、各具完整价值的多重声音,被有机缝合为一个完整叙事空间的时候,历史与现实、个体与族群、此时与彼时的密切呼应就得以宏大而具实、精深而鲜活地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燕食记》“出虚入实,虚实相生”的故事叙述方式,本身又构成了历史与当下的对话复调。这种三重叙事复调互融互衬的叙事策略,彰显出作者深厚精湛的艺术功力。
《宝水》的叙事结构采用的是“春夏秋冬”的四时节序。小说分为四个章节,虽是按四时节序顺序写来,作者却并未将“春夏秋冬”四季截然分开,而是特别突显了四时节序之间的相互缠绕与勾连。第一章是冬—春;第二章是春—夏;第三章是夏—秋;第四章是秋—冬,真正是理得顺却捋不清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是因为只有在农村原乡,春暖花开、夏阳明朗、秋实丰饶、冬雪冰寒等自然风景的区分度虽然特别明显,与之密切相连的人情事理和节令习俗的差异性也特别鲜活,但无论是春夏之交还是秋冬之交,时节交替的节奏却是相对缓慢的,缓慢的节奏内连着农人们相对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不像城市里夏季一到,从商场到酒店,从办公室到家里,空调就会轰隆隆地运转起来,而冬季一到,暖气就会输送到上述各个地方,很是整齐划一;二是因为只有在农村老家的日常生活中,才随处可感可知那些纠结着血缘地缘、恩义嫌隙、打断骨头却还连着筋的祖奶外婆、七姑八姨、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之间的复杂关系,才更能见出传统文化中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为牵扯的绵延与融合。由此,乔叶成功创造出的这个“宝水村”,成为新时代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或者说一个典型案例,更由此建立起一个具有鲜明独特性的文学场域和地标。小说语言散发出一种生猛鲜活的乡土味,人物对话土里土气却又生动传神,既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又特别契合人物个性。
《回响》选用的是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交织推进的叙事结构。明线,是按照冉咚咚率领刑侦队侦破“大坑案”的计划一步步推进的;暗线,则沿着冉咚咚探查丈夫慕达夫背着她在宾馆开房之真相而一层层铺开。换言之,明线是冉咚咚对外寻求案件的真相,暗线是冉咚咚对内寻求真我。两条线索频繁交织密切呼应且互为参照。而形成参照的主要原因是东西将“二律背反”手法巧妙地运用在明暗两条线索的交织推进过程中,使女刑警冉咚咚随时随刻深陷既自信又自卑的矛盾纠结里难以自拔。在明线推进层面,侦破工作的每一次突破,都表现出冉警官的聪慧、机敏、果决;但在暗线展开层面,所谓的真相每一次被证实不过是她的妄猜和臆想,都诠释了冉警官面对日常生活时情商掉线的可悲可叹。作者对冉咚咚随时以职业的侦破思路与技能,去侦探自己的家庭生活的行为举止,进行了深刻而尖锐的剖析,警醒批判之意不言而喻。这种“奇数章写刑侦推理,偶数章写爱情心理”的叙事策略,既有类型文学的叙事流畅、可读性好的特点,又有纯文学带给人深刻思辨与审省的优点。
概括而言,上述五部小说在思想艺术层面所呈现出的鲜明特色与优长,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浓妆淡抹皆相宜。五位作家可贵的创新探索和精妙的叙事策略,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立足新时代新语境文学书写的新征程,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必将迎来更美好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