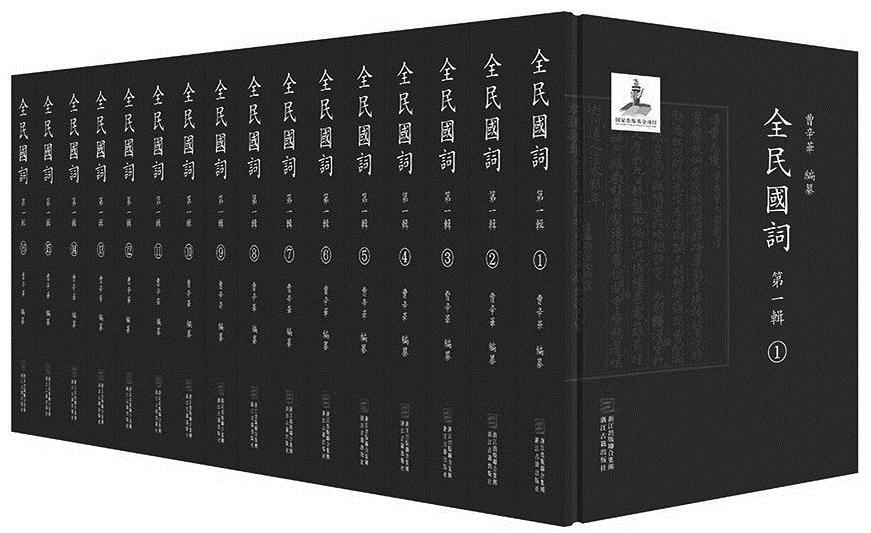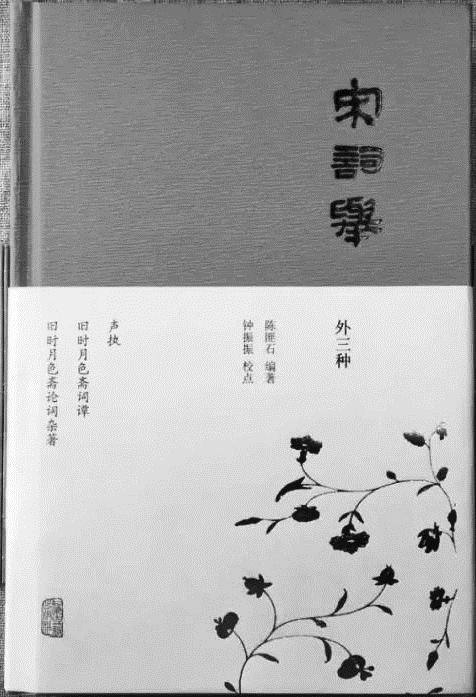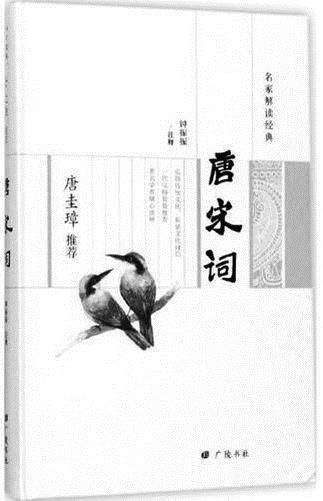□主讲人:钟振振
主讲人简介:
钟振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韵文学会荣誉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常务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俄罗斯、美国、德国、澳大利亚、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数十所著名高校、研究机构及文化团体讲学。业余从事诗词、楹联、文言文创作,撰有《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赋》《瓮安赋》《苏州湾吴江太湖新城赋》《重修南京夫子庙记》《江苏发展大会乡贤纪念林碑铭》《安徽马鞍山采石矶三台阁楹联》《新疆伊犁汉家公主纪念馆门联》等。诗词、楹联作品曾多次在海内外诗词、楹联大赛中荣获特等奖、一等奖。
编者的话:
中华经典诗文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发展,积淀着丰富的情感和智慧,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标识,也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的宝贵资源。古往今来,诗词无时无刻不在人们的生活当中,是人们诗意人生的写照、家国情怀的寄托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艺术结晶。传承好诗词文化,对安顿个体心灵、涵养民族精神和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丰富广泛,思想情感丰沛饱满,是创作诗词的重要素材。创作诗词也是传承古典诗词的重要方式。本期讲坛邀请钟振振教授讲述古典诗词的现代传承。
传统诗歌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中华民族是诗性的民族,是有诗意的民族。传统诗歌(广义的诗歌包括词在内)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基因。
诗是什么?诗是一种表达方式。通俗一点讲,就是“说话”。人有思想,有感情,有生活,有喜怒哀乐,愿意与他人交流,愿意与他人分享,就要“说话”;或者,有意见、建议与诉求,也要“说话”。不同的是,普通的“说话”,我说、你听;我说清楚了、你听明白了,“说话”的任务就完成了。而诗,则是用更凝练、更审美、更优雅、更睿智、更有技术含量,从而也更高级的语言或方式来“说话”。能用诗来“说话”的民族,一定是更文明、更有智慧、更有文化修养和文化品位的民族。中华民族,正是这样的一个民族。
至迟,上古时代的唐尧时期,距今4500年左右,已经有诗。如《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如果说它出自后人的记录,还不足以凭信的话,那么2500年前的《诗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凿凿可据,不容置疑。其中有西周初年的作品,距今已3000多年了。其所达到的艺术高度,令人叹为观止。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蒹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采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无衣》)“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采葛》)至今脍炙人口,仍是中国传统诗歌的典范。此后,有楚辞,汉魏晋南北朝以来的乐府、古诗,以及唐宋以来的近体诗与词、元以来的曲,一直传承、发展到今天,中国传统诗歌历经千年而生生不息。
有一年,我应邀赴广西桂平采风,在当地的龙潭森林公园里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一群野生猕猴组成的“丐帮”,“拦路抢劫”游客手里的纯净水,并且喝得有滋有味。于是即兴写了一首七言绝句:“缒壁投崖跳掷轻,诸猴可哂是精灵。清溪满谷矿泉水,偏劫游人唾剩瓶。”这显然不是在嘲笑猴儿,而是借这件趣事为由头,用比兴手法来善意批评那些对中国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熟视无睹,不知道珍惜、开发和利用的人。
我们都是中华诗词这一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基因的传承者,承担着中华诗词继往开来、发扬光大的历史使命,任重道远。我们必须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无愧于时代的作品来!
说到这一点,我认为有两种偏颇的倾向是需要克服的。一种是,一味强调继承,而忽视创新。有人以为,当代诗词创作的最高境界,是放到唐宋人的诗词集里可以乱真。我认为,当代诗词创作的最高境界应是,即便放到唐宋优秀作家的诗词集里去,也能够活蹦乱跳地“窜”出来,一看就是“当代”诗词,而且是优秀的“当代”诗词。当代诗词创作不说胜过古人,至少不应是古人的“优孟衣冠”。“一生低首谢宣城”,应该是“战术行为”,而绝不是我们的“远大目标”。
另一种是,只顾埋头创作,而忽视继承。不熟读历代诗词,怎么知道古人的诗词创作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怎么知道古人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诗词创作的要诀,我认为要“识好歹”。识得好歹,创作便有标准,成竹在胸,出手自然不凡;不识好歹,写一万首也只是原地踏步。这三个字,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却很难。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每天坚持,以七分的时间和精力阅读,三分的时间和精力习作,要“思”,更要“悟”,那么终会有豁然开朗的一天。到那时,自然“下笔如有神”。这就是“观千剑而后识器,操千曲而后晓声”!
我自十一二岁起读诗写诗,迄今已60多年,悟出这三个字来,一生受用不尽。
如何用传统语汇书写现代题材
如何用旧体诗词这种中国诗歌的传统体裁来写中国社会的现代题材,是当前诗词创作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有人认为,既然是写传统诗词,当然只能用古已有之的语汇,用现当代的新语汇入诗,就是“离经叛道”。只要在诗里用了现当代的新语汇,不管写得怎样,他们一律不承认这也是诗。这种态度对不对呢?我认为不对。其所以不对,是因为它不符合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文学语言也是与时俱进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永远凝固在某一个历史时代。如果汉代的人坚持认为不能用汉代的新语汇来写诗,那还会有汉乐府吗?如果唐人坚持认为不能用唐代的新语汇来写诗,那还会有唐诗吗?如果宋人坚持认为不能用宋代的新语汇来写词,那还会有宋词吗?如果元代的人坚持认为不能用元代的新语汇来写曲,那还会有元曲吗?那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古代诗歌,就都是先秦的《诗经》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了。如按照某些“喜旧厌新”者的逻辑去推论,连他们写的那些“像唐诗”“像宋词”的作品也不能算“诗”了,因为它一点也不“像《诗经》”。
同样的情况,古人也有。例如北宋词人宋祁,他差点当上了“高考状元”。当年的进士科举考试中,他是尚书省礼部考试的第一名。只不过在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考试“殿试”时,由于他哥哥宋庠也考得不错,皇上认为弟弟名次排在哥哥前面不大好,就把状元给了他哥哥宋庠。宋祁确实是个大才子,可就是有个“毛病”,过于“好古”。他修《新唐书》,把前人《旧唐书》里许多浅近的语句都改得古奥艰深了。比如唐代名将李靖的传记,《旧唐书》里引用了李靖一句话,“疾雷不及掩耳”。这句话,晋朝人写的《三国志》、唐人修的《梁书》《隋书》《北史》里都有,已经是成语了。可宋祁还认为它语言太新,不够古雅,偏要改成“震霆无暇掩聪”。为此,他的领导、领衔主持修《新唐书》的欧阳修还委婉地批评了他。今天我们看到的《新唐书》,这句改成了“震霆不及塞耳”。看来,宋祁还没有完全接受欧阳修的“批评”。比起“震霆无暇掩聪”来,“震霆不及塞耳”要通俗一点了,但还是不如原来的“疾雷不及掩耳”既通俗又好。总之,语言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正确的文学语言史观应该是“喜新”而“不厌旧”。
用旧体诗词来写现代题材,难度不在于格律——因为旧体诗词中的近体诗和词虽然要讲格律,但古体诗却比较自由,并不受格律的束缚。如果用旧体诗词来写现代题材的难度仅仅在于格律,那么不写近体诗或词,专写古体诗,问题岂不是解决了?其实,用旧体诗词来写现代题材的难度,主要在于语汇的选择和运用。现代社会日新月异,新事物、新思维、新观念层出不穷,新名词、新概念、新语汇(包括许多外来语)批量涌现。如果不分青红皂白,都往诗词里搬,与诗词中旧有的传统语汇搅和在一起,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不古不今,亦土亦洋,让人怎么看了怎么别扭。当然,不是说现当代语汇包括外来语不可以用,而是要注意对此类新语汇的使用要慎之又慎,要反复斟酌。倘若新语汇本身具有形象性(至少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形象性),用用自亦无妨;如果是抽象的概念,略无形象可言,一般来说,最好不要轻易拈出。此外,在使用新语汇时,要特别注意与传统语汇的磨合,力争做到水乳交融,相得益彰。
用新语汇入旧体诗词既然较为艰难,那么,只用传统语汇是否有可能完成现代题材的诗词创作呢?我的体会是:完全可能。旧体诗词语言的艺术张力,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局促有限,它几乎是“无事不可入、无意不可言”的!
许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我写了一首七言绝句《中秋对月怀台海故人》:“海峡鸿沟五十年,一衣带水即天渊。西楼夕夕东南望,看得中秋月又圆!”诗意是说:台湾海峡成为“鸿沟”已经50多年了,一条窄如衣带的水域竟使得两岸隔绝,判若天渊。每天晚上,我都向着东南方眺望,眼睁睁地看得中秋的月亮又圆了一回。我曾多次到台湾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访问讲学,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朋友。寒舍位于四楼,阳台面向东南。每天晚饭后,我都要在阳台上小坐片刻,或备课,或写诗,或构思论文。偶一抬头,便看到月亮冉冉升起。这时,往往会想起海峡对岸的朋友。“看得中秋月又圆”,话外的意思是:什么时候海峡两岸的骨肉同胞才能够团圆呢?全中国人民对于两岸统一、骨肉团圆的期盼,是重大的现代题材。我的这首小诗,并没有使用任何新语汇,也表达出了心声。
这首小诗只是用“赋”(直说)的手法来写,如用“比兴”(比喻)手法来写,则传统语汇对于现代题材进行艺术表现的主动权就更大了。现代题材一经处理为灵活巧妙的比喻,便可转化成传统语汇应付裕如、游刃有余的相关内容,作者不必再为新语汇难以运用而犯愁。
再以我的另一首七言绝句为例,《海归吟》:“冰川溶泄静无痕,谁纤黄河向海奔?便到重洋也蒸汽,归云作雪壮昆仑。”(小序:海外学人归国报效者日众,学界简称其为“海归”。)诗的字面意是说:昆仑山的冰川悄无声息地消融着,水滴汇成了黄河。是谁用纤绳拉着她奔向大海?黄河的水啊,即便流入了重洋,还是会蒸发上天,化作雨云飞回中国,变为飘飘雪花降落在昆仑山上,使得巍巍昆仑更加雄伟壮观。由于诗题和小序已经交代了主旨,它的深层意蕴也就不言自明了。我虽然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但也有在海外访学一年多的生活体验,因此深切了解众多海外中国学人对祖国铭心刻骨的热爱,对故乡与日俱增的眷念。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的出国留学热潮,到近年来海外学人纷纷回归报效祖国的盛况,数十年的时间跨度,上千万人的流动规模,这样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如此重大的现代题材,假如不借助于“比兴”并使用传统语汇,而是直赋其事并掺用现当代新语汇,区区28个字如何概括得了?又怎么能够达到形象鲜明、姿态横生、诗味苞含、耐人咀嚼的艺术效果?
当然,这类“比兴”体的诗词,题目的作用也是很关键的。全篇都是“谜面”,题目才是“谜底”。倘若诗题不揭出“海归吟”三个字,那么读者就只能照字面义去理解,将这首诗看成是一篇用韵语创作的旨在说明“冰—水—雨云—雪—冰”自然循环过程的科普小品了。因此,诗的正文是“画龙”,而题目则是“点睛”,神光所聚,不可不留心。
当代诗词的创作与传承
诗词创作的最高标准,是“真善美”。这是“王道”,包罗万象,包容万有。老子说“大象无形”,什么是世间最大的“象”?是宇宙。宇宙有形状吗?没有。所以它能包罗万象,包容万有。但“无形”的东西,便不可捉摸,只能抽象地说,无法具体地说。要说得具体,就不能“形而上”,只能“形而下”。有诗友要我讲诗词创作的“巧思”,“巧思”不是“王道”,是“霸道”;不是“形而上”,是“形而下”;不是诗词创作的最高标准,只是较高标准之一。
“巧”是常用词,人人明白,无须下定义。但我觉得有必要从时常与其搭配的另外一些字面来思考,如“奇巧”之“奇”、“巧妙”之“妙”、“精巧”之“精”、“新巧”之“新”、“灵巧”之“灵”,等等。诗词创作,不奇不妙不精不新不灵,就谈不上“巧”。舍“奇妙精新灵”而专求其“巧”,必然弄巧成拙,画虎不成反类犬。
这里所说的“思”,主要指“构思”。构思通常是就谋篇立意这个大局来说的,这是其内含。但也不妨外延,扩大化来说,雕章琢句,烹词炼字,也需要“思”。论诗词之结构,无非字、词、语、句、章、篇;论诗词之内容,无非人、物、情、景、事、理。凡此种种,如欲出彩,无一不须巧妙构思,精心结撰。
诗词创作的构思,最重要的是谋篇立意,就是要有创意。初学者的注意力或兴奋点,往往在字句,喜欢堆砌华丽的辞藻。如唐人王昌龄的《观猎》诗:“角鹰初下秋草稀,铁骢抛鞚去如飞。少年猎得平原兔,马后横捎意气归。”诗里的那个少年,洋洋得意,不过是打了几只兔子!试比较王维的《观猎》:“风劲角弓鸣,将军猎渭城。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忽过新丰市,还归细柳营。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诗中的这位将军,志不在得“平原兔”,而在射云中雕——眼界要高得多。总之,字句、辞藻不是不重要,但它毕竟只是“平原兔”,不是云中雕。它毕竟是“战术”层面的问题,而创意才是“战略”层面的问题。
唐代杜牧《答庄充书》说:“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未有主强盛而辅不飘逸者,兵卫不华赫而庄整者。四者高下圆折步骤,随主所指,如鸟随凤,鱼随龙,师众随汤武,腾天潜泉,横裂天下,无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辞句绕前捧后,是言愈多而理愈乱,如入阛阓,纷纷然莫知其谁,暮散而已。是以意全胜者,辞愈朴而文愈高;意不胜者,辞愈华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辞,辞不能成意。大抵为文之旨如此。”他说的虽然是写文章,不是写诗词,但道理都是一样的。
说到诗词创作的巧思,就不能不谈诗词创作时要注意“立意”“词句”“格律”三者的关系。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写香菱拜林黛玉为师学作诗,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
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
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得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的诗上,亦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的,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没事的,只要词句新奇为上。”
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
这段对话的核心观点是:“立意”最为要紧,“词句”次之,“格律”又次之。只要“意趣真”,“词句”不用修饰也是好的;果真“词句新奇”,“格律”不合(平仄出入、对仗欠工)也尽使得。话虽说得极端了一些,但究其本质而言,却是高明的见识。曹雪芹这里说的只是律诗,举一反三,则格律诗词都可包括在内。要知道,“格律诗词”四字,如作语法分析,是一个偏正结构,意思是“讲究格律的诗词”,中心词是“诗词”,“格律”不过是个定语。明白这一点,谁主谁次,岂不了然?倘若一首诗词意思陈旧,语句平庸,饶你写得平仄调和,句法妥当,对仗安稳,押韵合辙,从形式上看中规中矩,一点毛病都没有,我们也只能遗憾地说:你写的是“格律”,不是“好”的“诗词”!相反,倘若一首诗词意趣真切、构思新颖,或遣词精警、造句奇妙,那么即便格律有所乖忤,瑕不掩瑜,也还不失为佳作。“格律”有所乖忤的佳作,好比蕴玉之璞,是可以打磨的;而“立意”不好,“词句”乏善可陈的作品,就只能推倒了重来,连修改的基础也没有。因此,有志于诗词创作的朋友,在一开始学习写作的时候,便应注意摆正“立意”“词句”“格律”这三者的主从关系,千万不要本末倒置,买椟还珠。也就是说,首先把写作的“兴奋中心”放到诗词主题的创意和艺术构思上来;其次再考虑怎样烹字炼词、安章宅句;至于是否符合格律,暂时不去管它。有了好的“立意”,有了好的“词句”,一首诗词便成功了一多半,那时再对照“格律”精细加工,未为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