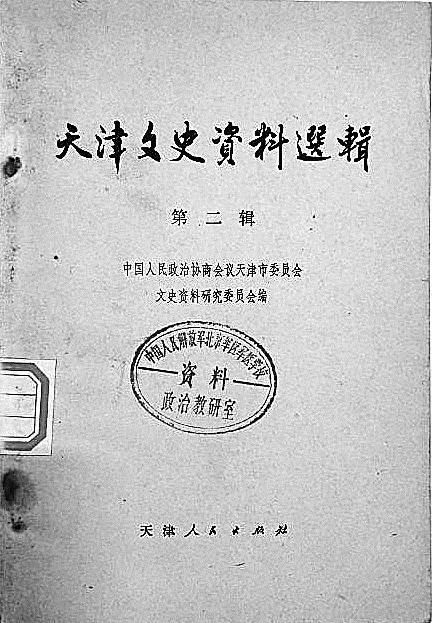1927年4月6日,张作霖控制的安国军政府搜查苏联大使馆,并逮捕了共产党人李大钊。4月28日,军政府在看守所里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秘密杀害,舆论一片哗然。
为了搪塞舆论,张作霖出版了《苏联阴谋文证汇编》,抛出一批苏联政府在中国搞“赤化”并组织政变的证据。此书中的材料后来广泛被传播引用,给李大钊的名誉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直到51年后,天津市文史资料选辑发表的一篇文史资料,才把历史的真相揭露出来。
李大钊在苏联使馆内被捕
1926年4月,张作霖入主北京,自任陆海军大元帅,并成立了安国军政府,力主“讨赤”,他的部下李景林甚至公然宣称“不问匪不匪,只问赤不赤”。
1926年4月24日,安国军政府以“宣传赤化,毒害社会,贻误青年”的罪名,杀害了《京报》社长邵飘萍。8月6日,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下令逮捕《世界日报》的成舍我、《民主晚报》的成济安。
此时,李大钊作为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中国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是冯玉祥国民军与国共两党的重要联络人,自然成为“讨赤”的重要目标。1926年9月中共中央给北方区委来信,要求李大钊等去武汉创建武汉区委;也有人劝他到天津去避避风头,但李大钊坚持留在北京,并决定带领国共两党北方机关及全家迁入苏联驻华大使馆继续工作。
根据《辛丑条约》,使馆区享有治外法权,中国军警不准入内,有一定的安全性,此前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曾在使馆区避过难。
李大钊等人进入苏联大使馆的行踪很快被京师警察厅侦知,张作霖便以“俄国人正在滥用使馆区的庇护,组织叛乱”为由,派出安国军总司令部外交处长吴晋为特使,与西方各国驻华公使进行接洽,请求准许军警进入东交民巷使馆区进行搜查。
外交使团首席公使欧登科于1927年4月4日召开秘密会议,以苏联已经退出《辛丑条约》为理由,不再享有领事保护权利,于是各国公使同意了安国军政府的请求。
1927年4月6日是清明节。上午11时,150多名警察、100多名宪兵全副武装,从警察厅出发分路直奔东交民巷,包围并控制了苏联大使馆。此前已有数十名便衣警察在使馆周围监视。
当时正在苏联使馆内工作的李大钊等人在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大钊的妻子共产党员、国民党员赵纫兰及其子女,以及苏联使馆工作人员60余人;抄走文件共463个卷宗,3000多份文件。
“李无确供”,从容就义
李大钊被捕后,一场社会各界的大营救活动开始了。苏联政府也对奉系的张作霖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
4月9日,政治讨论委员会开会,到会40余名委员认为:“此次东交民巷事件,较为重大,各国观瞻所系,若非正式交付法庭,而仅由军法裁判,其结果将贻法权委员会以领事裁判权不宜交还之重大口实,实于国家前途贻害甚大。”决定推举梁士诒、杨度为代表,并邀罗文干一起往见张作霖。
杨度于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他还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在上海时还通过孙中山认识了李大钊。因此李大钊被捕后,他断然以4500大洋低价卖掉了自己的住所“悦庐”公馆,全力营救李大钊出狱。在杨度的奔走呼号下,很多名流、进步人士参与了营救李大钊。
章士钊则直接找到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请他转告张作霖:“切不可为一时意气杀戮国士。”曾在北洋法政学堂任教的范熙壬,与李大钊亦师亦友,得知李大钊被捕的消息,连续两次探访安国军总参议杨宇霆未果。1927年4月9日夜,给杨宇霆写了《致杨邻葛督军书》,劝其“消弭内争,协力对外”,不要“同胞相残”。
李大钊同乡挚友白眉初闻讯后,悲愤地大声疾呼:“大钊是讲社会学的,不讲主义讲什么?难道讲主义有罪?难道只兴这班强盗讲杀人主义、卖国主义?”遂以北京师范大学史地部主任名义,找该校董事长,并联络李书华等同乡及在京教育界名流,积极进行营救活动。
4月10日下午,北京国立九校校长在法大三院开会,议决自10日起,由各校分途营救李大钊一案被捕人员。11日,北大校长余文灿、北师大校长张贻惠访张学良,适因公外出,由秘书代见,提出:李大钊系属文人,请交法庭依法审问;李大钊之妻女,请即释放等条。
乐亭同乡李时、白眉初、武学易、李采岩等300多人,联名上书陈情,要求张作霖放过李大钊,释放其妻子儿女。
当时国内各报都有消息发布,如《申报》《晨报》《北京日报》《民国日报》《大公报》《顺天时报》《东方时报》《北京益世报》《北洋画报》等,《世界日报》更是逐日跟踪报道。
警察厅一方面对外界宣称“李大钊口供颇多”,但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4月23日,由于张作霖对此“党案”不敢进行公审,便决定派参议何丰林就任审判长,组成由军方控制的特别法庭,不顾各界人士和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对,宣判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死刑。28日上午11时,张作霖决定在看守所里使用绞刑对李大钊等20人秘密行刑,下午1点执行。
李大钊临刑时毫无惧色,第一个走上绞架,从容就义。
抛出伪证混淆视听
当天下午,张作霖为了向各国公使证明杀害李大钊的合法性,邀请“各外使参观党案文件,昨日下午偕赴警厅”。而实际上,张作霖始终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苏联“赤化”中国的证据,也没能从李大钊口中得到共产党组织工农暴动的证据。
苏联政府也发表声明称,那些文件都很普通,在任何一国的使馆里都能得到。张作霖竟然在没有确证的情况下将李大钊等人绞杀,引起社会舆论一片哗然。
1927年5月以后,张作霖只得一面下令加大文件公布的数量,并专门成立了一个“查获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调动政府中所有懂外文的人对这些文件进行编译,并向社会不断公布所谓文件“证据”。
“查获苏联阴谋文件编译会”的主任叫张国忱,1898年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哈尔滨俄国商业专门学校毕业,俄文非常好。张作霖对他非常信任,称他为“自己家乡的孩子”,故将他调到东三省交涉总署交际处工作,后调张家口任外交部特派察哈尔交涉员。
张作霖派人搜查苏联大使馆后,为了找到共产国际在中国搞“赤化”的“罪证”,急调张国忱到北京任编译会主任,令其一方面将苏联大使馆抄来的所有文件翻译出来,以找到“赤化”铁证;同时将这些文件编辑成《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书广为散发。
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后,张国忱任张学良秘书,后任东三省交涉总署首席参事兼交际处处长、镇威上将军府咨议、东三省交涉总署顾问兼东省特别区教育厅厅长等职。1931年任天津市财政局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大学俄文教授。
“精诚所至”探真相
1975年,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恢复。当时,急需找一些人从事文史资料征集,于是有人推荐当时正处于生活困顿中的柴寿安前去。
柴寿安是一位很干练的女性,新中国成立前,曾在1947年创刊的天津《新星报》做过记者,文笔很好,思维敏捷,该报在天津解放前夕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了。柴寿安是记者出身,对采访很在行,因而对征集文史资料很有兴趣,也很投入。同时,她也是资深民盟成员,工作中她结识了同是民盟成员的天津美术出版社编辑张鸾,而张鸾正是张国忱的女儿。
柴寿安从张鸾口中得知了其父张国忱的经历,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而且关系相当密切,他一定知道很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秘闻”。于是柴寿安请张鸾引见,想登门拜访这位深居简出的老者,当时张国忱已年逾80岁。
但当时“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消除,很多人,特别那些曾被认为是“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是心存余悸,不但不想讲述过去的事情,更不敢实事求是地讲过去历史曾发生的事情,因此文史资料征集工作很难做。尽管全国政协文史委多次要求要解放思想,积极抢救史料,但在具体工作中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当柴寿安提出请张国忱先生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自然遭到谢绝。张国忱说自己眼睛患白内障,写不了东西了。柴寿安说可以录音方式来做,而张国忱说自己年事已高,过去的事情已记不清楚了。所以这个史料的征集过程始终进展不顺利。
后来,柴寿安多次到家里找张鸾聊天,在交往的过程中,发现张鸾当时因工作很忙,有时顾不上照顾张国忱的生活起居。于是柴寿安主动提出为张鸾分忧,帮张国忱烧水喂药、洗衣做饭,搀扶他外出晒太阳,甚至在张国忱卧床不起时,还帮他清理屎尿等。
柴寿安的举动令张国忱非常感动,以至说柴寿安像自己亲生女儿一样。俗话说:“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张国忱终于同意敞开心扉对柴寿安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了。
经过多次细致耐心的采访,柴寿安最终于1978年10月完成对张国忱的史料征集任务,写出《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一文,发表在1979年《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上。
因为这篇史料的重点是写张作霖父子在中东路问题上的对苏交涉,故对《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事着墨不多,但也足以说明问题了。
迟到51年的真相
张国忱在《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一文中这样叙述:
(1927年)四月六日,张作霖派出军警发动了对苏驻华大使馆的搜查,逮捕了李大钊等多人,同时查获相当多的档案、书籍,各国文字都有。张作霖命陈兴亚迅速到各机关将凡懂外文的人都调来,尽快译出。陈兴亚遂组织了编译会,正好原驻海参崴总领事兼奉天代表王之相从海参崴回来,陈遂请王为编译会主任。张作霖知道后,不大满意地说:“打电报把张国忱找来,叫他星夜兼程来京。”
在搜查后的第三天,我急忙从张家口赶来,到京后立即晋见张作霖,他在斗纸牌 (张作霖素爱斗天津卫的纸牌),看见我,放下纸牌说:“俄国大使馆叫我捜查了,东西全在警察厅,他们组织个编译会,我不信任他们,你去吧,由你当会长。”又说:“文件、档案什么都有,要造底册,每天译出的东西,要油印出来,给我送十份。叫他们给你发个红车牌,随时可以进新华门。”
过了十几天,张作霖又找我说:“这些天翻出来的东西没多大意思,没有向国际上宣传赤化的材料,要注意查找,这样可以激起国际上的注意。”
我回去后心想,翻了这么多日子,哪有啊?译员中有外国记者,我找了一个老白俄,是哈尔滨《喇叭报》的记者。我叫他假造一份向国际宣传赤化的材料,由王之相译出,给张作霖送去,搜查苏眹大使馆的这一件公案就算告一段落。
据柴寿安自己所写回忆文章记载,当时张国忱回忆细节说:
我找来一个白俄记者米塔列夫斯基,是哈尔滨《喇叭报》主编,他和我很熟悉,这次也被我约来参加编译会工作,我要他按要求伪造一份文件,他勉强答应了。总算搞到一台与搜查出的文件所用同型号的打字机,俄国造的纸有的烧焦了,有的用水浇得变样了,只好用新的,尽量做些假装。伪造件制成后,由王之相翻译,王在俄文原件上写了“极要文件”四个字,译好后,送交张作霖。从此,好几天,张没再找我。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的同志考虑到当时《天津文史资料选辑》尚是刚出刊的“内部发行”书刊,不会有大问题,因此就发表了。
“铁证”成伪证
《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一文发表后,引起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习五一的注意。当时,她正借调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写作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华民国史》的第二编第五卷。她看到了“内部发行”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注意到上面刊登的这篇《张作霖父子当权时对苏关系和中东路内幕》一文,对其中的这些细节产生兴趣,并手持近代史所的介绍信,专门到天津访问张国忱,并请他确认《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中伪造的材料。
天津市政协文史委的柴寿安热情地接待了她。在柴寿安的引荐下,张国忱对这套书的来龙去脉做了较细致的介绍,并一一指认了书中伪造、不实之处,之后,他还在指明之处签名画押,以保证他所讲的真实性。张国忱对柴寿安说:“我对伪造的文件记忆犹新,因其对历史研究会有影响,故特作以上交代和说明,以供历史研究者参考。”
习五一回京后,结合其他研究资料,写了《苏联“阴谋”文证〈致驻华武官训令〉辨伪》一文,并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2期发表,文章细致地分析考证并揭露了这个《苏联致驻华武官训令》,这是一份假文件:由外国公使教唆、张作霖授意、张国忱和白俄记者作伪而炮制出笼。
相似的内容,后来又以《张作霖伪造共产国际文件真相》为题,在《民国春秋》1987年第1期再次披露。
张作霖以伪造的文件,来掩盖他杀害李大钊等20位革命志士的罪行,真相最终大白于天下。《苏联阴谋文证汇编》这个曾被日法美英等国认定的“铁证”,被一篇历史当事人的文史资料变成了伪证,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本文作者为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