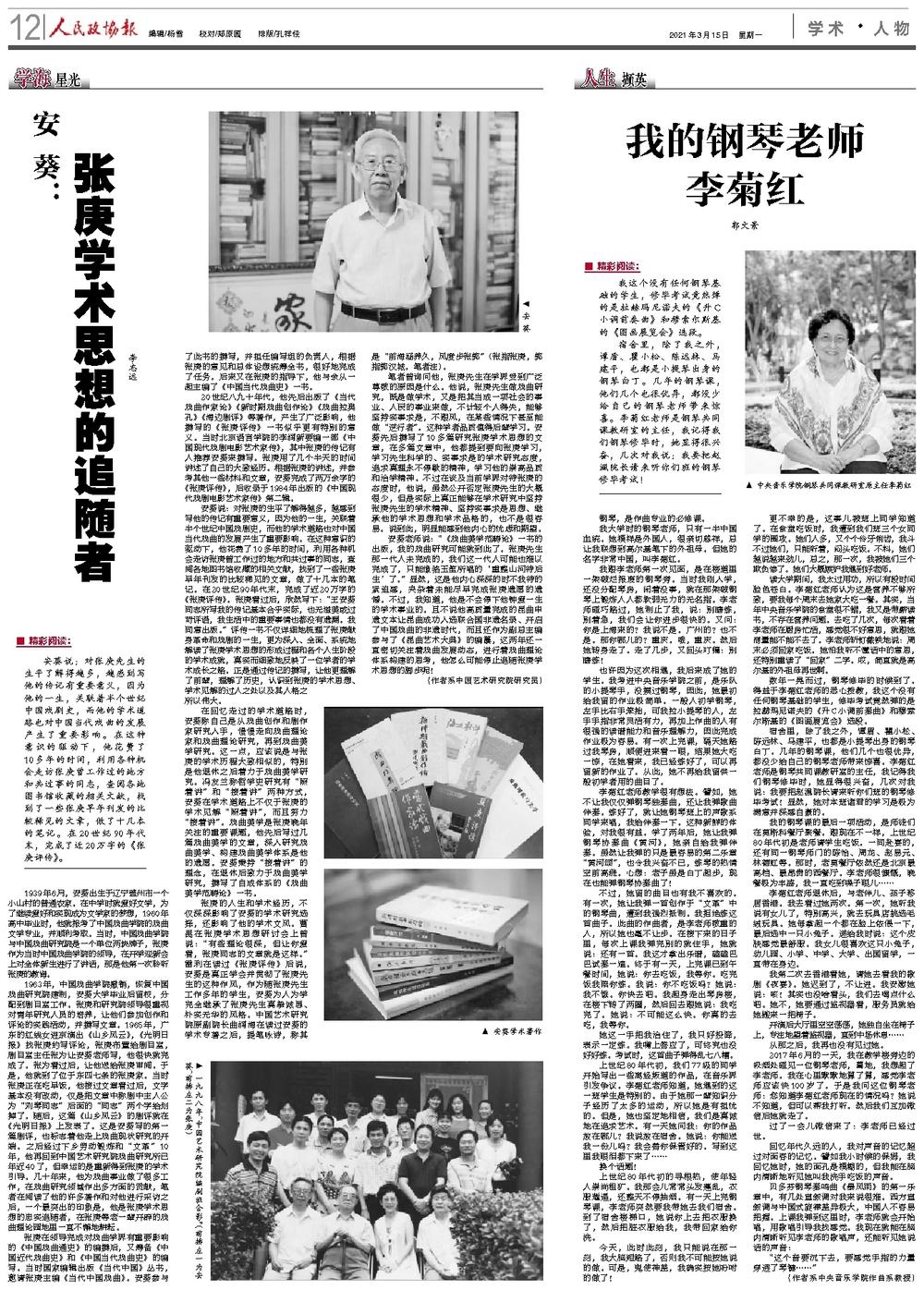郭文景
■ 精彩阅读:
我这个没有任何钢琴基础的学生,修毕考试竟然弹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选段。
宿舍里,除了我之外,谭盾、瞿小松、陈远林、马建平,也都是小提琴出身的钢琴白丁。几年的钢琴课,他们几个也很优异,都没少给自己的钢琴老师带来惊喜。李菊红老师是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主任,我记得我们钢琴修毕时,她显得很兴奋,几次对我说:我要把赵渢院长请来听你们班的钢琴修毕考试!
钢琴,是作曲专业的必修课。
我大学时的钢琴老师,只有一半中国血统。她模样是外国人,很亲切慈祥,总让我联想到高尔基笔下的外祖母。但她的名字非常中国,叫李菊红。
我跟李老师第一次见面,是在楼道里一架破烂报废的钢琴旁。当时我刚入学,还没分配琴房,闲着没事,就在那架破钢琴上锻炼人人都软弱无力的无名指。李老师碰巧路过,她制止了我,说:别瞎练,别着急,我们会让你进步很快的。又问:你是上海来的?我说不是。广州的?也不是。那你哪儿的?重庆。哦,重庆。然后她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叮嘱:别瞎练!
也许因为这次相遇,我后来成了她的学生。我考进中央音乐学院之前,是乐队的小提琴手,没摸过钢琴,因此,她最初给我留的作业极简单。一般人初学钢琴,左手比右手笨拙,可我拉小提琴的人,左手手指非常灵活有力,再加上作曲的人有很强的读谱能力和音乐理解力,因此完成作业极为容易。有一次上完课,隔天她路过我琴房,顺便进来看一眼,结果她大吃一惊,在她看来,我已经练好了,可以再留新的作业了。从此,她不再给我留供一般初学者用的曲目了。
李菊红老师教学很有想法。譬如,她不让我仅仅弹钢琴独奏曲,还让我弹歌曲伴奏。练好了,就让她钢琴班上的声歌系同学来唱,我给伴奏一下。这种新鲜的体验,对我很有益。学了两年后,她让我弹钢琴协奏曲《黄河》,她亲自给我弹伴奏。虽然让我弹的只是最容易的第二乐章“黄河颂”,也令我兴奋不已,练琴的热情空前高涨。心想:老子虽是白丁起步,现在也能弹钢琴协奏曲了!
不过,她留的曲目也有我不喜欢的。有一次,她让我弹一首创作于“文革”中的钢琴曲,遭到我强烈抵制。我拒绝练这首曲子。此曲的作曲者,是李老师敬重的人,所以她也毫不让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每次上课我弹完别的就住手,她就说:还有一首。我这才拿出乐谱,磕磕巴巴试奏一遍。终于有一天,上完课已到午餐时间,她说:你去吃饭,我等你。吃完饭我陪你练。我说:你不吃饭吗?她说:我不饿。你快去吧。我起身走出琴房楼,在楼下转了两圈,然后回去跟她说:我吃完了。她说:不可能这么快。你真的去吃,我等你。
她这一手把我治住了,我只好投降,表示一定练。我嘴上答应了,可终究也没好好练。考试时,这首曲子弹得乱七八糟。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77级的同学开始写出一些离经叛道的作品,在音乐界引发争议。李菊红老师知道,她遇到的这一班学生是特别的。由于她那一辈知识分子经历了太多的运动,所以她是有担忧的。但是,她也坚定地相信,我们是真诚地在追求艺术。有一天她问我:你的作品放在哪儿?我说放在宿舍。她说:你能送我一份儿吗?我会替你保管好的。写到这里我眼泪都下来了……
换个话题!
上世纪80年代初的寻根热,使年轻人崇尚粗犷。我那会儿常常头发蓬乱,衣服邋遢,还整天不停抽烟。有一天上完钢琴课,李老师突然要我带她去我们宿舍。到了宿舍楼梯口,她说你上去把衣服换了,然后把脏衣服给我,我带回家给你洗。
今天,此时此刻,我只能说在那一刻,我大脑短路了,否则我不可能按她说的做。可是,鬼使神差,我确实按她吩咐的做了!
更不幸的是,这事儿被班上同学知道了。在食堂吃饭时,我遭到我们班三个女同学的围攻。她们人多,又个个伶牙俐齿,我斗不过她们,只能听着,闷头吃饭。不料,她们越说越来劲儿,总之,那一次,我被她们三个欺负惨了。她们大概嫉妒我遇到好老师。
读大学期间,我太过用功,所以有段时间脸色苍白。李菊红老师认为这是营养不够所致,要我每个周末去她家大吃一餐。其实,当年中央音乐学院的食堂很不错,我又是带薪读书,不存在营养问题。去吃了几次,每次看着李老师在厨房忙活,感觉很不好意思,就跟她商量能不能不去了。李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周末必须回家吃饭。她怕我听不懂话中的意思,还特别重读了“回家”二字。哎,简直就是高尔基的外祖母再世啊。
数年一晃而过,钢琴修毕的时候到了。得益于李菊红老师的悉心授教,我这个没有任何钢琴基础的学生,修毕考试竟然弹的是拉赫玛尼诺夫的《升C小调前奏曲》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选段。
宿舍里,除了我之外,谭盾、瞿小松、陈远林、马建平,也都是小提琴出身的钢琴白丁。几年的钢琴课,他们几个也很优异,都没少给自己的钢琴老师带来惊喜。李菊红老师是钢琴共同课教研室的主任,我记得我们钢琴修毕时,她显得很兴奋,几次对我说:我要把赵渢院长请来听你们班的钢琴修毕考试!显然,她对本班诸君的学习是极为满意并深感自豪的。
我的钢琴课的最后一项活动,是师徒们在莫斯科餐厅聚餐。跟现在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初是老师请学生吃饭。一同赴宴的,还有同一钢琴师门的陈怡、周龙、赵易元、林德虹等。那时,老莫餐厅依然还是北京最高档、最昂贵的西餐厅。李老师很慷慨,晚餐极为丰盛,我一直吃到嗓子眼儿……
李菊红老师退休后,与老伴儿、孩子移居香港。我去看过她两次。第一次,她听我说有女儿了,特别高兴,就去玩具店挑选毛绒玩具。她每拿起一个都在脸上依偎一下,最后选中一只小兔子。递给我时说:这个皮肤感觉最舒服。我女儿很喜欢这只小兔子,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出国留学,一直带在身边。
我第二次去香港看她,请她去看我的歌剧《夜宴》。她迟到了,不让进。我安慰她说:咳!其实也没啥看头,我们去喝点什么吧。她不,她要通过监视器看,服务员就给她搬来一把椅子。
开演后大厅里空空荡荡,她独自坐在椅子上,专注地望着监视器,直到中场休息……
从那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2017年6月的一天,我在教学楼旁边的吸烟处碰见一位钢琴老师,蓦地,我想起了李老师。我在心里默默地算了算,感觉李老师应该快100岁了。于是我问这位钢琴老师:您知道李菊红老师现在的情况吗?她说不知道,但可以帮我打听。然后我们互加微信后她就走了。
过了一会儿微信来了:李老师已经过世。
回忆年代久远的人,我对声音的记忆超过对面容的记忆。譬如我小时候的保姆,我回忆她时,她的面孔是模糊的,但我能在脑内清晰地听见她叫我洗手吃饭的声音。
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暴风雨》的第一乐章中,有几处宣叙调对我来说很难。西方宣叙调与中国式旋律差异极大,中国人不容易把握。上课我弹到这里时,李老师就会开始唱,用歌唱引导我找感觉。我现在就能在脑内清晰听见李老师的歌唱声,还能听见她说话的声音:
“这个音要沉下去,要感觉手指的力量穿透了琴键……”
(作者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