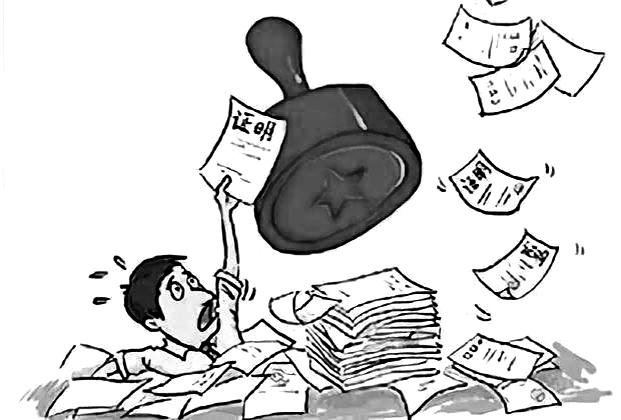本报记者 徐艳红
2月28日,本报《人大代表、法学专家回应网友留言——出具含行政违法记录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于法无据》一文刊发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关注,“今日头条”上评论数近5000条。3月10日,全国两会闭幕当天,几位网友还寄来了一面写有“人民政协报 为人民发声”的锦旗。为此,本报记者拨通了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的电话,邀请两位专家对网友关切再次作出回应。
——编者
肖胜方代表: 治安处罚是行政违法不是犯罪
3月14日,记者联系到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律师协会会长肖胜方,他说,《出具含行政违法记录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于法无据》一文刊发后,有治安处罚包括前科经历的人给他发来很多短信以表达感激之情,有的写得还很长。
肖胜方看到留言后,并没有过多地谈论原来的话题,而是说:“从网友留言可以看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存在的最大问题是:分不清治安处罚和犯罪。”
“违法”一词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违法按其性质和危害程度的不同,可分为刑事违法、民事违法和行政违法。刑事违法就是犯罪,对社会危害较大,是违法中最严重的一种;轻微违法行为,尚达不到刑事处罚标准的,可以进行行政处罚(治安处罚),属于行政违法行为;民事违法行为,就是侵害了他人的民事权利,需要进行赔偿或承担其他责任的行为。狭义的违法则是指犯罪以外的一般违法。平常多表达的是其狭义。“也就是说,犯罪一定违法了,但并不是所有的违法都是犯罪。但社会上很多人将二者混淆了。”肖胜方说。
关于前科制度,肖胜方表示,为预防犯罪,我国现行刑法第100条规定了前科报告制度,即“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对于犯罪记录的查询,最高法、最高检、公安、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印发过《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从法律角度而言,只有犯罪人员才有前科,治安处罚人员并没有规定。
肖胜方强调,“对于国家司法机关而言,法无授权即应禁止,就是说国家法律没有授权的事,政府部门就不能做。”那么,法律没有授权公安机关为公民出具“无违法记录证明”,基层派出所就不能层层加码地将“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成“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
此外,肖胜方表示,不少人都有持有类似网友“@么么你”这样的看法——“自己做的孽就要承担作孽的后果”,认为成年人违法了就要承担后果,这也是很多人不支持治安处罚记录消灭的共同想法。肖胜方说,一方面,“违法要承担后果”没错,但他们接受治安处罚已经承担了自己违法的后果,比如,行政拘留5日不就是违法受到的处罚吗?另一方面,不少网友都将犯罪与违法画等号,混淆了概念,有的网友只看标题,并没有看完全文内容就发表评论,这样往往容易出现偏差。
另外,肖胜方表示,不少网友关心建议的进展情况,他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相信相关部门会认真对待该建议。“推进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一蹴而就,相关部门承办也需要时间,要有耐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我国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也是国家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和主攻方向,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之一,我们一定要有信心。”肖胜方最后说。
彭新林教授:
将感性的道义与刚性的法律相融合是司法文明大势所趋
《出具含行政违法记录的“无犯罪记录证明”于法无据》一文刊发后,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也收到了不少反馈,他说,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来自有治安处罚记录的人员,他们大都表达了激动之情,表示对个人未来的发展更有信心,并热切希望包括专家学者、代表委员在内的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关注这个问题,关注他们面临的就业、生活等现实困境,期望对于治安处罚记录能有明确统一的规定,或是期限、有条件地消除,或是封存,不要在开具“无犯罪记录”时附录上治安处罚的记录。当然,也有人依然焦虑和迷茫,急切想了解有关部门对此事的态度。
另一种情况则来自学界同仁的关注。彭新林表示,有专家看了报道后表示:治安处罚记录引发的不利后遗效应值得高度关注,专家学者、代表委员们和《人民政协报》做了一件关乎民生的有意义、有价值的好事。其实,该报道刊发后,彭新林已经撰写了一篇3000字左右的要报稿件,及时报送给了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研究会,受到了该会高度重视。
彭新林看到网友们在“今日头条”上的留言后也承认,对于治安处罚记录的问题说明社会上并未达成共识。他分析有几个不可忽视的原因:一是对治安处罚记录消灭存在认识上的思维惯性或是误解。有人以为,治安处罚记录消灭就意味着不区分情况的即时消灭,而且习惯性地认为治安处罚记录消灭必然会增加社会不安全感。“实际上,就域外国家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来说,无论是依申请人请求启动消灭还是司法机关依职权消灭,都设置有法定的消灭条件(包括时间条件和表现条件),大都要求申请人在一定期间内表现良好,对社会安全的担忧是没有必要的。”彭新林表示。
二是报应观念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报应观念的影响下,不少人认为违法人员承受各种规范内外的不利影响甚至歧视,似乎是“罪有应得”“咎由自取”“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报应观念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但却并非人类理性的产物。应当倡导宽恕的价值理念,为治安处罚记录消除提供有力的文化支撑。
三是对治安处罚人员存在普遍性的社会歧视心理。这种社会歧视心理会给他们复归社会带来重重障碍。在某种意义上讲,治安处罚记录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惩罚,正因如此,有必要采取有力措施来推动消除社会歧视心理、树立公平对待违法犯罪记录人员的思想观念。
彭新林认为,解决治安处罚案底后遗影响的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短期内估计还有不少难度,对此他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不仅是立法上能否做出相关制度安排的问题,也涉及到行政支持、司法保障、观念转变等多方面的因素,同时还需要统筹考虑治安处罚记录消灭与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衔接问题。从长远来看,通过消灭治安处罚记录的办法,将感性的道义与刚性的法律相融合,为有违法犯罪记录的人员提供发展空间,排除其就业、生活等方面的障碍,本身就是一种将其拉回社会怀抱而非冷酷地推向歧途的善举,是人道主义的具体体现,也是司法文明的大势所趋。”
彭新林表示,需要指出的是,对治安处罚记录带来的各种消极影响和不利后遗效应,解决治安处罚案底只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而不是唯一途径。除了治安处罚案底,完全可以综合施策,积极寻求其他替代性救济措施。多种措施综合运用往往比单一的消灭或者封存治安处罚记录更为有效,可能会获得更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