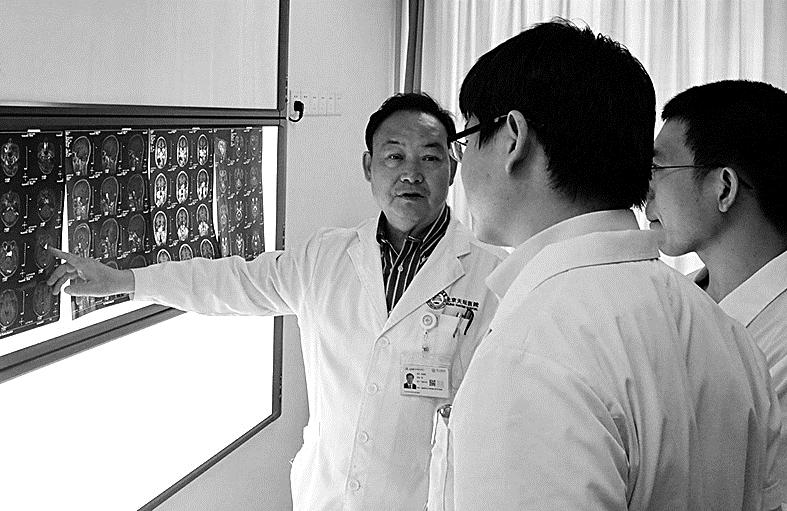我于1977年毕业参加工作。那时候我们班同学基本都留在了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带我们的医生前辈和我们大约相差十来岁,这也就意味着神经外科医生断档了将近十年。
攻坚克难挺进手术禁区
刚参加工作时的场面给了我很大的触动。当时神经外科有一个病房中的八个患者全是昏迷状态,也就是现在所指的“植物人”。他们只能切开气管,通过鼻饲喂水、喂奶,还需要他人帮助翻身、吸痰。这些患者中有的三五个月后便去世了,有些患者则需要在病床上躺很久。当时不管是诊断水平还是手术水平,都处于较差的阶段,而且人们对于神经外科的认识不够,也没有现在的安全意识。我记得那时候脑瘤比较少,往往都是高血压和脑出血,还有很多是由于不戴安全帽从房顶掉下来造成的脑损伤,或是由于在工厂头发卷到机器里造成的头皮撕裂伤等。我见到的患者基本都属于比较严重的,再加上不断转院导致病理诊断不明确等原因,最后好不容易转到能做手术的医院,却因为耽误了时间而医治无效。
真正让我对外科产生兴趣的是一批老前辈,他们之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我的老师王忠诚院士,他当时五十多岁,不仅是神经外科主任,还是医院院长。纵然面对这么不乐观的前景,他还是毅然决然地坚持发展神经外科,不断提高诊断治疗技术,挽救了很多患者,这种精神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1982年,我随王忠诚院士迁至北京天坛医院神经外科工作。同年,我加入了王忠诚院士负责的“脊髓内肿瘤和脑干肿瘤”攻关项目组,对这一领域进行开创性的研究。那时候,全国能做脑外科手术的医院寥寥无几,1982年大规模开展工作后,我们逐渐有了进口CT、核磁等先进的诊断设备。但是当时我们与国外的交流很少,导致脑外科的学术信息相对封闭,同时也没有足够多的参考病例或书籍,诊治经验相对不足,即使在硬件不断进步的情况下,我们也面临着诸多困难。
脑外科和普通外科不一样,普通外科可以通过触诊感觉到是否有包块或者哪里疼痛,但是脑子却没有办法通过触摸的方式诊断,只能通过临床或者开刀来进行分析。在开展研究的初始阶段,我们能够引用的病例只有一二十例,结果非常不好,不仅面对社会有很大的压力,同行之间也出现了质疑的声音,都认为大脑是一片禁区。
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医疗水平,比如逐步把脑干肿瘤切除率提高到40%,并不断改善放疗和化疗的方案。我们通过患者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到现在为止,很多当时设定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脑干肿瘤也做到了全切除,患者术后恢复的效果也非常好。
临险不惧挽救疑难病患
那时候我们的研究条件非常艰苦,还出现了很多意料不到的问题。其中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案例是一位延髓肿瘤术后的睡眠综合征患者。患者白天的时候意识很清醒,肢体活动能力也很好,但是一睡觉就没有呼吸,这种情况多达十几次。延髓是管呼吸功能的,那时候还没有呼吸机,我们只能安排三个护士每人8个小时,看住患者不让他睡觉。后来,我们逐渐地摸索到问题的来源,术前患者睡眠有呼吸但是术后没有呼吸,那说明手术过程中肯定触及了他控制呼吸的地方。脑干肿瘤通俗一点形容就像一个小小的白萝卜,手术中你很难判断出具体的神经核团在什么地方,只能靠摸索,这依赖于临床的案例总结。如果不小心触及了控制呼吸的地方,患者就会出现呼吸障碍;如果不小心触及了其他的地方,还会有嘴歪等情况。
在我们开展脑干的血管母细胞瘤和巨大的脑膜瘤治疗之后,有很多华侨回国治疗,其中一位患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脑膜瘤患者,几乎双目失明,三四个月之前在国外做过一次手术,由于肿瘤切除困难,只切除了冰山一角,患者失血将近4000ml,这相当于成年人的总血液量。回国后,他到天坛医院找到我,我发现他的肿瘤巨大,直径达到8cm。由于肿瘤供血极其丰富,并且包绕着重要的神经血管,我们与患者共同讨论过多次,想到之前在美国只切除了一点就造成大量的失血,我们也没有把握把它全部处理掉,因此当时十分纠结。但是我们认为,国外不能做的,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做,最后还是决定实施手术。那时候王忠诚院士已经70多岁,整整12个小时一直在身后陪着我们,虽然60多岁的患者在手术台上有几次血压降到零位,输血量达到1100毫升,但是到最后我们实现了全切肿瘤,患者的眼睛重见光明。之所以有很多华人华侨回国治疗,是因为在脑干肿瘤和颅底肿瘤的治疗上,我国在世界外科领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妙手仁心宽慰患者忧虑
我国的医疗水平有地区的差异,很多患者在相对落后的地区看病时,由于没有医疗条件且风险系数较高,医生一般都会交代得非常严重,严重程度足以让患者和家属放弃治疗。但还是会有一些患者抱着一线希望来北京想听听我的意见,有时候我看到患者的情况说:“你这可以做啊,你不做就没有希望,你这是做手术的病,不是吃药打针的病。”
医生的影响力不是靠电视宣传,而是靠老百姓之间的口口相传,特别是现在患者群体越来越庞大,增加了患者之间相互传播的影响力。这是我们努力的动力,因为患者的推动有助于我们越做越好。如果一个患者严重到很多医生都放弃了,只有我没放弃,等手术后患者恢复正常,没有出现想象中的坏情况,我会非常有成就感。
很多患者都是在关键的地方开刀,这个过程压力很大,一方面原因是患者大多比较年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很多患者慕名而来,直接表明要找张大夫看病,甚至让我保证患者手术之后和现在一样,不会出现偏瘫、嘴歪等症状。其实我可以理解患者的心情,但是由于病情不同,我们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手术后的情况,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不让患者留遗憾。
从第一次开始做手术到现在,我已经做了上万台手术。上了手术台,就需要精神高度集中,我从来不会想是否劳累。每次做完手术后,不论是简单的还是复杂的,我回到家躺在床上都会把整个手术过程再回忆一遍,这是为了寻找经验教训。我经常教育年轻同志要养成这个习惯,因为我们即使会在术前与患者交代术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但不能理所应当地认为患者就要承担后果,不能不总结经验,不然下一个患者可能还会出现问题。
神外手术比较复杂,有时会直接牵扯到患者的生活质量,比如出现面瘫、嘴歪等。尤其是比较年轻的患者,如果面部出现问题就可能不愿出门、不愿与社会打交道了,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到患者的心理状态,尽量杜绝这方面的问题。有些人可能性格比较开朗,能够面对疾病,但是有些人就无法面对,哪怕只是得一个良性肿瘤,想到需要对脑袋进行手术,内心也无法接受。所以,作为医生,我们要学会如何开导患者。
春风化雨培育医学新锐
现在我们之所以在颅内肿瘤的诊治方面取得成绩,不是某一个人的工作水平有多高,而是整个团队的作用。天坛医院发展到如今的规模,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队伍的传承。很多时候我做手术主要是为了带好年轻医生,他们是颅底脑干手术的主力,如果没人带他们,他们可能与我们年轻时一样,就需要在这条路上自己摸索。所以,我们是一点一滴地培养年轻医生,有时候他们看起来手术做得很成熟,但是与我同台手术后,就能看清楚应该如何改进。
我培养学生从来不会使用家长式耳提面命的管理,我的几十个学生都很优秀,不管是科研工作,还是论文发表,都有自觉性。其实,这也是一个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虽然教他们临床工作,但是好多东西我也需要向他们学习,比如外语、信息化技术的操作等。我们不能总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眼光来看待现在的年轻人,现在80后的年轻人承担了很多国家重大项目,他们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群体。
天坛医院神经外科义诊团基本每年都要去外地义诊交流,我们还利用互联网进行疑难手术的全国高清视频直播。比如台湾的神经外科同行到福建时,就曾做过手术演示。由于是实时转播,操作的每个细节都会清晰地呈现在大屏幕上,因此对业务能力的要求比较高,所以我们必须对基本功有信心和决心。其实,我们每次的手术都非常复杂,也有很大的压力,要注意到手术当中的各个细节,并做好充分的准备。目前为止,我做了很多特别复杂的手术,基本没有恐惧感,更多的是成就感。我认为手术就像是艺术,我享受其中。
从医47年,让每一位患者不留遗憾,一直是我努力的动力。落实到医生这个职业,则需要我们有责任感、有治病救人的思想。当前,很多事情都与市场挂钩,比如先进设备如果回报率不高,它可能就不会被研发出来。但是医生不能这样思考,无论我们的技术如何,对待患者都需要换位思考,需要有医德。
(张俊廷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天坛医院主任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