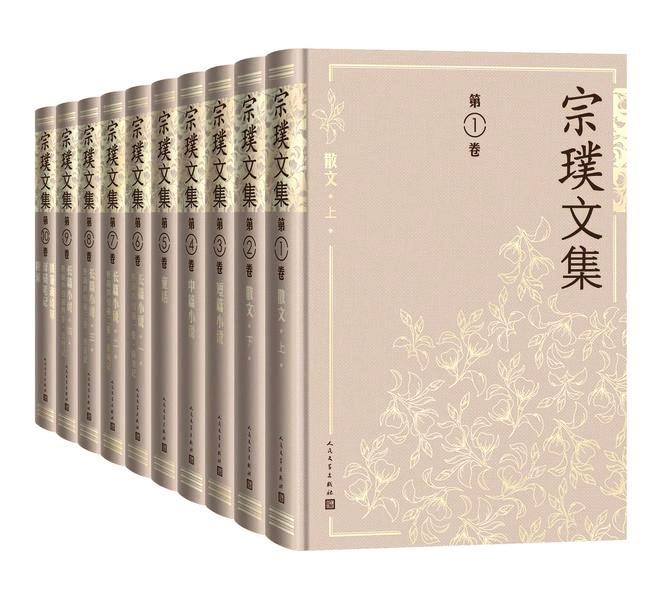■7月26日是作家宗璞96周岁生日,7月27日,宗璞创作八十年暨《宗璞文集》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从事文学创作80年来,宗璞以笔耕不辍的精神,为当代文坛奉献了文质兼美的小说、散文、童话、诗歌作品,并以“诚”与“雅”的文学品格书写了20世纪知识分子赤诚而坚韧的家国情怀。
和宗璞大姐相识,已有44年之久。那时还在北大读书,宗璞大姐住在燕南园。其时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重放的鲜花》。王蒙、李国文、邓友梅、流沙河等人的作品也都在经历了一个特殊时期之后如鲜花般再次绽放了。宗璞的《红豆》也是其中的一篇。看过那几朵“重放的鲜花”,真有振聋发聩之感。用当下的眼光,或许很难理解我们当时所获得的冲击力——一个纯真的女大学生江玫,在新的时代和新的人生即将开始之时,做了艰难的抉择。其中,人性的复杂、情感的纠葛,岂不是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但在发表《红豆》的年月,革命道路的选择,岂容些微的动摇与彷徨?更不允许纠结于感情的取舍。《红豆》的回归,对我有关文学的认知,特别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认知,已经算是极大的挑战了。便想着得认识这位用《红豆》向僵死的文艺教条发出挑战的宗璞大姐。而后来见到的宗璞大姐却温婉得很,首先她在文友面前,永远是一个倾听者。我知道大姐无论是个人阅历还是有关中外文化方面的积累,都远超于我。但这四十几年的交往中,我从未见过她高谈阔论,倒是我总在那儿神侃。一想起那时光,就自责自己何以不正襟危坐一点儿,哪怕学点儿也行。
宗璞大姐是温婉的,却又是风趣的、率真的。我领教的一次,是她忘情山水时的率真。大约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钟山》编辑部组织,搞了一次“太湖笔会”,由时任《钟山》掌门人刘坪和总编辑徐兆淮组织,同船泛舟的还有汪曾祺、林斤澜、刘心武、宗璞、理由、母国政,或还有哪位,记不起了。一行数人由苏州登船,驶往无锡的鼋头渚,那太湖的风光确让宗璞沉醉了。开心,更因为大家都是相亲相重的友人,便使太湖之游成为一次心无挂碍口无遮拦的旅行。事后,读到宗璞的一篇回忆汪曾祺的散文,记下了汪曾祺在船上口占七绝开玩笑的故事。文中写道:“时光一晃过了40年。八十年代初,《钟山》编辑部举办太湖笔会,从苏州乘船到无锡去。万顷碧波,洗去了尘俗烦恼,大家都有些忘乎所以。我坐在船头,乘风破浪,十分得意,不断为眼前景色欢呼。汪兄忽然递过半张撕破的香烟纸,上写着一首诗:‘壮游谁似冯宗璞,打伞遮阳过太湖,却看碧波千万顷,北归流入枕边书。’”宗璞又说:“我曾要回赠一首,且有在船诸文友相助,乱了一番,终未得出究竟。而汪兄这首游戏之作,隔了五年,仍清晰地留在我记忆中。”记得当时汪老的诗是我们在场每一位传览过的,每一位读者,无不喝彩。我记得宗璞大姐当场也依韵打油了一首的,雅谑处处可与汪老绝句相得益彰。其中专有一句是幽我一默的。年代久远,已经记不得了。或许宗璞也记不得了,因此她也只好在文末写道:“乱了一番,终未得出究竟。”如今,宗璞大姐已年届九十六,记得冯友兰先生当年曾为金岳霖先生撰写寿联,说:“何止于米,相期以茶。”而今,宗璞大姐早已把米寿甩在了后面,正在我们的目光下“相期以茶”,而我也已奔七十五之龄。回忆40年前那开心一幕,仍然是止不住的欢喜。
宗璞又是直率的,直率到甚至不顾老弟“人模狗样”的面子。大约应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一次春节慰问。那时我已调到中国作协担任一点行政职务。春节将至,自然也承担了部分走访任务。走访的对象,是包括宗璞大姐在内的几位老作家。走访时的礼物,也简单得很——一盒点心,是作协下属某单位食堂自制的,再加一束花。登门、拱手、寒暄、拜年,同行的,是好几位作协的干部,有熟的,也有不熟的,拜年是诚心的,深聊是不可能的。万没想到一天下来,晚上就接到宗璞大姐的电话,说晚间就把那点心尝了,不错不错,感谢感谢,只是告诉你,那萝卜丝饼的馅儿是臭的!打电话给你,一是感谢,一是告知,勿再以此饼慰问。至嘱至嘱。切切。我的天呐,谁知道哪个环节,铸此大错。不过我知道大姐之坦诚,是为我好,也为作协好。大姐岂会挑我的理儿。旧事重提,也算是姐弟情深,了无尘埃的一个案例。
宗璞大姐的文学成就涉及多个方面,恕不一一。我敬重她直抒胸臆、顽强拼搏的坚韧。1987年底,她终于完成了《野葫芦引》第一部《南渡记》的写作,她自述写作“这两年的日子是在挣扎中度过的……不管怎样,只能继续挣扎上前。”就这么又“挣扎”了两年之后,第二部《东藏记》完成,她自述说自己“两年间写写停停,侍奉老父。生了一场病,且战且行。”她总是“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而且因为目疾,只好借助口授,完成了这本书。2001年,宗璞大姐开始《西征记》的写作,其间她承受着失去“第一位读者”蔡仲德先生的巨大悲痛,完全借助于口授,历时8年完成了《西征记》,此后,又10年,她终于完成了《野葫芦引》的最后一部《北归记》,我记得捧读《北归记》的后记,忍不住热泪盈眶,因为宗璞大姐说,“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十字路口奋斗……需要奋斗的事还很多,要走的路还很长,而我,要告别了。”我认为,大姐这一番话,堪比太史公《报任少卿书》所叹,自古富贵而名磨灭者,不可胜记,惟倜傥非常之人称焉。宗璞大姐应属倜傥非常之人中的一个。她在完成了自己的神圣使命之后,不免一声叹息。这叹息是一位96岁老人的如释重负。想到这,我不知道大家感受如何。
我只能照搬古人所说,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作者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