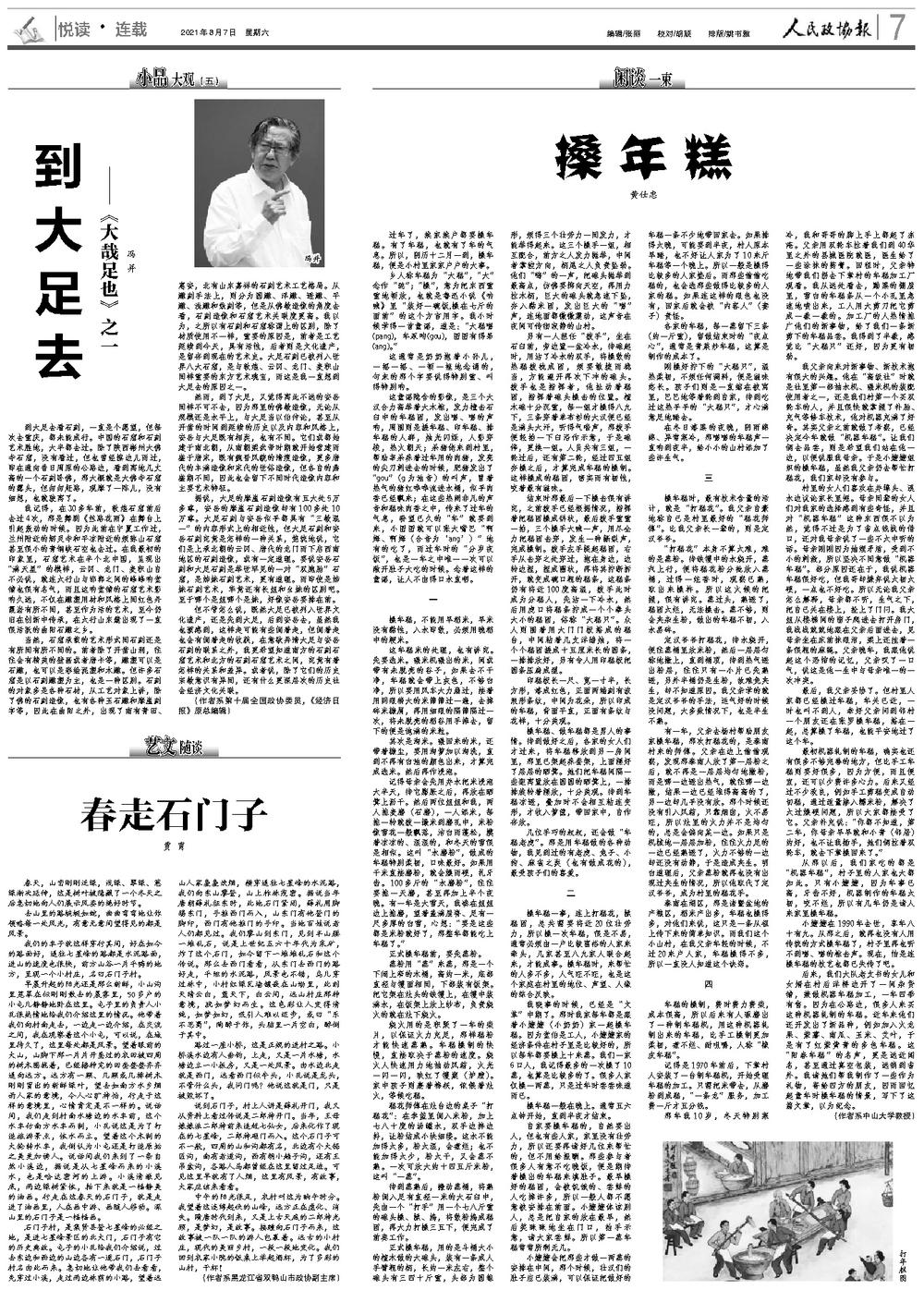冯并
到大足去看石刻,一直是个愿望,但每次去重庆,都未能成行。中国的石窟和石刻艺术胜地,大半都去过。除了陕西彬州大佛寺石窟,没有看过,但也曾经擦边儿而过,即在通向昔日周原的公路边,看到离地几丈高的一个石刻卧佛,那大概就是大佛寺石窟的露头,但匆匆赶路,观摩了一阵儿,没有细想,也就驶离了。
我记得,在30多年前,敦煌石窟前后去过4次,那是舞剧《丝路花雨》在舞台上引起轰动的时候。因为此前在宁夏工作过,兰州附近的炳灵寺和平凉附近的须弥山石窟甚至很小的青铜峡石空也去过。在我最初的印象里,石窟艺术在半个北中国,呈现出“满天星”的模样,云冈、龙门、麦积山自不必说,就连太行山与邯郸之间的峰峰响堂铺也很有名气,而且这响堂铺的石窟艺术影响久远,不仅在雕塑用材和风格上同红色丹霞岩有所不同,甚至作为活的艺术,至今仍旧在创新中传承,在太行山东麓出现了一直很活跃的曲阳石雕之乡。
当然,石窟承载的艺术形式同石刻还是有所同有所不同的。前者除了开凿山洞,往往会有精美的壁画或者唐卡等,雕塑可以是石雕,也可以是彩绘泥塑和木雕。但许多石窟是以石刻雕塑为主,也是一种区别。石刻的对象多是各种石材,从工艺对象上讲,除了佛的石刻造像,也有各种玉石雕和摩崖刻字等,因此在曲阳之外,出现了南有青田、惠安,北有山东嘉祥的石刻艺术工艺格局。从雕刻手法上,则分为圆雕、浮雕、透雕、平雕、浅雕和线刻等,但是从佛教造像的角度去看,石刻造像和石窟艺术关联度更高。我以为,之所以有石刻和石窟称谓上的区别,除了材质使用不一样,重要的原因是,前者是工艺延续到今天,具有活性,后者则是文化遗产,是留存到现在的艺术史。大足石刻已被列入世界八大石窟,是与敦煌、云冈、龙门、麦积山同样重要的东方艺术瑰宝,而这是我一直想到大足去的原因之一。
然而,到了大足,又觉得离此不远的安岳同样不可不去,因为那里的佛教造像,无论从规模还是水平上,与大足当以伯仲论,甚至从开凿的时间到延续的历史以及内容和风格上,安岳与大足既有相类,也有不同。它们或都始建于南北朝,从南朝梁武帝时期就开始营建而盛于唐宋,既有魏晋风貌的清瘦造像,更多唐代的丰满造像和宋代的世俗造像,但各自的鼎盛期不同,因此也会留下不同时代造像内容和主要艺术特征。
据说,大足的摩崖石刻造像有五大处5万多尊,安岳的摩崖石刻造像却有100多处10万尊。大足石刻与安岳似乎都具有“三教混一”的内容形式上的相近性,但大足石刻和安岳石刻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笼统地说,它们是上承北朝的云冈、唐代的龙门而下启西南地区的石刻造像,或有一定道理。要说安岳石刻和大足石刻是举世罕见的一对“双胞胎”石窟,是姊妹石刻艺术,更有道理。而即使是姊妹石刻艺术,毕竟还有长姐和幺妹的区别吧。至于哪个是姐哪个是妹,好像安岳要排在前。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大足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还是先到大足,后到安岳去,虽然我也预感到,这样走可能有些倒着走,但倒着走也会有倒着走的收获,在意欲弄清大足与安岳石刻的联系之外,我更希望知道南方的石刻石窟艺术和北方的石刻石窟艺术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和差异。或者说,除了它们的历史宗教意识有异同,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历史社会经济文化关联。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