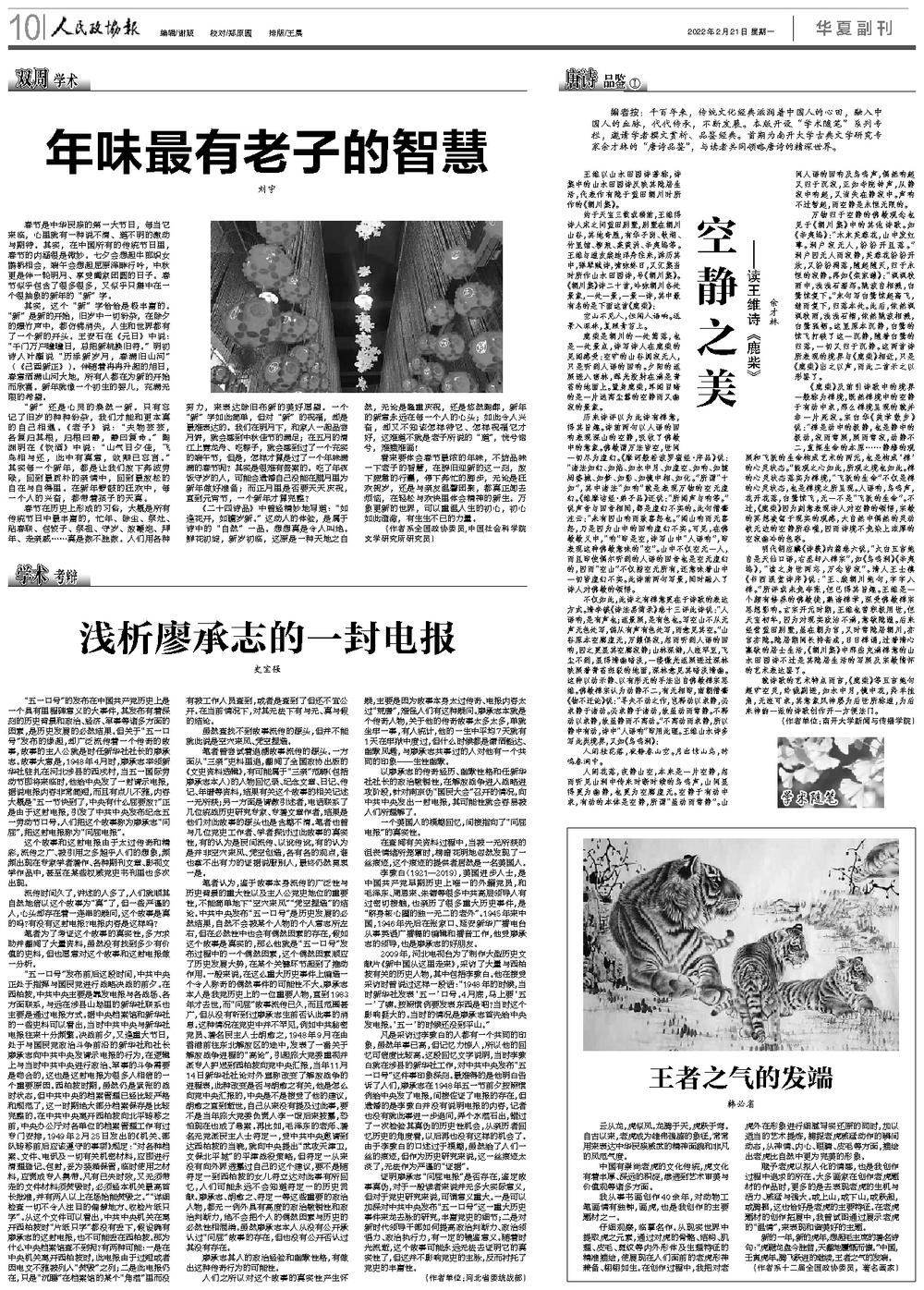史宝强
“五一口号”的发布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其发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因素,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关于“五一口号”发布的缘起,却广泛流传着一个传奇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廖承志。故事大意是,1948年4月时,廖承志率领新华社驻扎在河北涉县的西戌村,当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临时,他给中央发了一封请示电报,据说电报内容非常简短,而且有点儿不雅,内容大概是“五一节快到了,中央有什么屁要放?”正是由于这封电报,引发了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人们把这个故事称为廖承志“问屁”,把这封电报称为“问屁电报”。
这个故事和这封电报由于太过传奇和精彩,流传之广、被引用之多超乎人们的想象,频频出现在专家学者著作、各种期刊文章、影视文学作品中,甚至在某些权威党史书刊里也多次出现。
流传时间久了,讲述的人多了,人们就顺其自然地信以这个故事为“真”了,但一些严谨的人,心头却存在着一连串的疑问,这个故事是真的吗?有没有这封电报?电报内容是这样吗?
笔者为了考证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多方求助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虽然没有找到多少有价值的史料,但也愿意对这个故事和这封电报做一分析。
“五一口号”发布前后这段时间,中共中央正处于指挥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前夕。在西柏坡,中共中央主要是靠发电报与各战场、各方面联系,与远在涉县山坳里的新华社联系也主要是通过电报方式。据中央档案馆和新华社的一些史料可以看出,当时中共中央与新华社电报往来十分频繁。决战前夕,又逢重大节日,处于与国民党政治斗争前沿的新华社和社长廖承志向中共中央发请示电报的行为,在逻辑上与当时中共中央进行政治、军事的斗争需要是吻合的,这也是这封电报为很多人相信的一个重要原因。西柏坡时期,虽然仍是紧张的战时状态,但中共中央的档案管理已经比较严格和规范了,这一时期绝大部分档案保存是比较完整的。在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转移之前,中央办公厅对各单位的档案管理工作有过专门安排,1949年2月25日发出的《机关、部队转移前后应该遵守的事项》规定:“对各种档案、文件、电讯及一切有关机密材料,应即进行清理登记、包封,妥为装箱保管,临时使用之材料,应责成专人携带。凡有已失时效,又无须带走的文件材料须焚毁时,必须经本机关最高首长批准,并有两人以上在场始能焚毁之。”“详细检查一切不令人注目的偏僻地方、收检片纸只字”。从这个文件可以看出,中共中央机关在离开西柏坡时“片纸只字”都没有丢下,假设确有廖承志的这封电报,也不可能丢在西柏坡。那为什么中央档案馆查不到呢?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时,此电报由于过短或者因电文不雅被列入“焚毁”之列;二是此电报仍在,只是“沉睡”在档案馆的某个“角落”里而没有被工作人员查到,或者是查到了但还不宜公开。在当前情况下,对其无法下有与无、真与假的结论。
虽然查找不到故事流传的源头,但并不能就此说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
笔者曾尝试着追溯故事流传的源头。一方面从“三亲”史料里追,翻阅了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有可能属于“三亲”范畴(包括廖承志本人)的人物回忆录、纪念文章、日记、传记、年谱等资料,结果有关这个故事的相关记述一无所获;另一方面是请教引述者,电话联系了几位统战历史研究专家、专著文章作者,结果是他们对此故事的源头也是含糊不清。笔者也曾与几位党史工作者、学者探讨过此故事的真实性,有的认为是民间流传、以讹传讹,有的认为是并非空穴来风、凭空创造,各有各的观点,谁也拿不出有力的证据说服别人,最终仍然莫衷一是。
笔者认为,鉴于故事本身流传的广泛性与历史背景的重大性以及主人公党史地位的重要性,不能简单地下“空穴来风”“凭空捏造”的结论。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然不会被某个人物的个人意志所左右,但在必然性中也会有偶然因素的存在,假如这个故事是真实的,那么他就是“五一口号”发布过程中的一个偶然因素,这个偶然因素顺应了历史发展大势,在某个关键环节起到了推动作用。一般来说,在这么重大历史事件上编造一个令人称奇的偶然事件的可能性不大。廖承志本人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直到1983年才去世,而“问屁”故事流传已久,而且范围甚广,但从没有听到过廖承志生前否认此事的消息。这种情况在党史中并不罕见,例如中共秘密党员、著名民主人士胡愈之,1948年9月在由香港前往东北解放区的途中,发表了一番关于解放战争进程的“高论”,引起旅大党委重视并派专人护送到西柏坡向党中央汇报,当年11月14日新华社社论对外宣称改变了解放战争的进程表,此种改变是否与胡愈之有关,他是怎么向党中央汇报的,中央是不是接受了他的建议,胡愈之直到逝世,自己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要不是当年旅大党委负责人李一氓后来披露,恐怕现在也成了悬案。再比如,毛泽东的老师、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符定一,受中共中央邀请到达西柏坡的当晚,就向中央提出“武攻天津卫,文保北平城”的平津战役策略,但符定一从来没有向外界透露过自己的这个建议,要不是随符定一到西柏坡的女儿符立达对此事有所回忆,人们可能永远不会知道符定一的历史贡献。廖承志、胡愈之、符定一等这些重要的政治人物,都无一例外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和政治判断力,绝不会把个人的偶然因素与历史的必然性相混淆。虽然廖承志本人从没有公开承认过“问屁”故事的存在,但也没有公开否认过其没有存在。
廖承志其人的政治经验和幽默性格,有做出这种传奇行为的可能性。
人们之所以对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故事本身太过传奇、电报内容太过“荒唐”,难怪人们有这种疑问。廖承志本就是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传奇故事太多太多,单就坐牢一事,有人统计,他的一生中平均7天就有1天在牢狱中度过,但什么时候都是潇洒豁达、幽默风趣,与廖承志共事过的人对他有一个共同的印象——生性幽默。
以廖承志的传奇经历、幽默性格和任新华社社长的政治敏锐性,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针对南京伪“国民大会”召开的情况,向中共中央发出一封电报,其可能性就会容易被人们所理解了。
一个美国人的模糊回忆,间接指向了“问屁电报”的真实性。
在查阅有关资料过程中,当被一无所获的沮丧情绪所笼罩时,柳暗花明地忽然发现了一丝痕迹,这个痕迹的提供者居然是一名美国人。
李敦白(1921—2019),美国进步人士,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上唯一的外籍党员,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很多中共高层领导人有过密切接触,也亲历了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是“跻身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1945年来中国,1946年先后在张家口、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从事英语广播稿的编辑和播音工作,他受廖承志的领导,也是廖承志的好朋友。
2009年,河北电视台为了制作大型历史文献片《新中国从这里走来》,采访了大量与西柏坡有关的历史人物,其中包括李敦白。他在接受采访时曾说过这样一段话:“1948年的时候,当时新华社发表‘五一’口号。4月底,马上要‘五一’了嘛。按照惯例要发表东西是吧?当时这个影响挺大的。当时的情况是廖承志首先给中央发电报。‘五一’的时候还没到平山。”
凡是采访过李敦白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印象,虽然年事已高,但记忆力惊人,所以他的回忆可信度比较高。这段回忆文字说明,当时李敦白就在涉县的新华社工作,对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件事印象深刻。最难得的是他明白告诉了人们,廖承志在1948年五一节前夕按照惯例给中央发了电报,间接佐证了电报的存在,但遗憾的是李敦白并没有说明电报的内容,记者也没有就此事进一步追问,弄个水落石出,错过了一次检验其真伪的历史性机会,从亲历者回忆历史的角度看,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于李敦白的口述过于模糊,虽然给了人们一丝的痕迹,但作为历史研究来说,这一丝痕迹太淡了,无法作为严谨的“证据”。
证明廖承志“问屁电报”是否存在,鉴定故事真伪,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对于党史研究来说,可谓意义重大。一是可以加深对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来龙去脉的研究,丰富党史的细节;二是对新时代领导干部如何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有一定的镜鉴意义。随着时光流逝,这个故事可能永远无法去证明它的真实性了,但这并不影响党史的主脉,反而衬托了党史的丰富性。
(作者单位:河北省委统战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