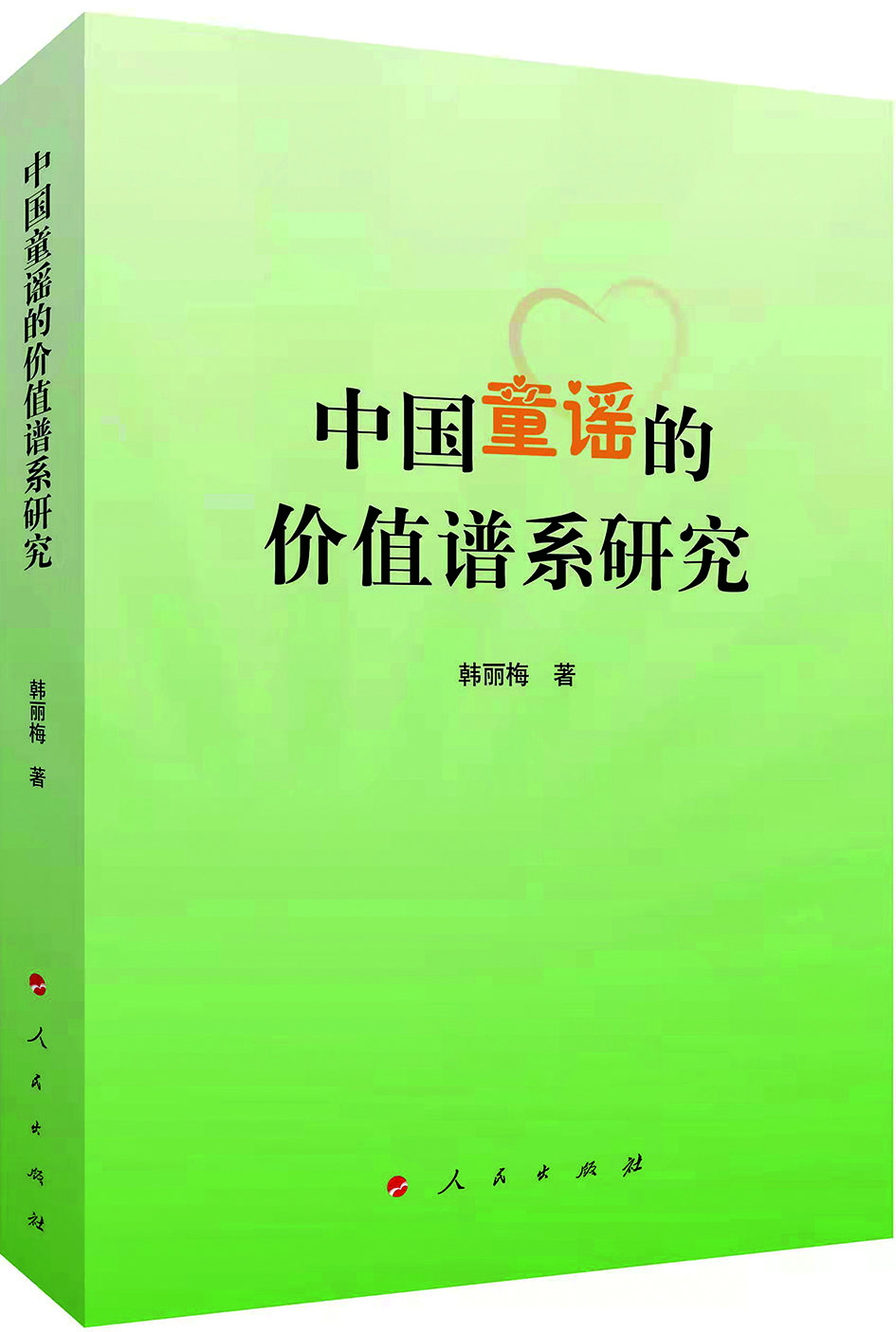何香久
童谣,指儿童歌讴之词,已有3000年的历史。明代以后,童谣逐步摆脱谶纬的束缚,最终实现了儿童本性的回归。从正统文学的视角来审视,童谣似乎永远不能说精致与经典。社会上有一说法,童谣浅显,小儿科,内容与技法一看就懂,主要为哄孩之用。可以想见,童谣虽走过了漫长的历史岁月,但难逃传统文人的所谓正统眼光的挑剔与讽刺。韩丽梅博士的新著《中国童谣的价值谱系研究》就童谣的历史演进及个性辨识进行了全面梳理,不在话下,然则在此基础上来进入相关的文学研究,追溯其悠久的历史,探检其在民间的丰富宝藏,自觉的理论思考中体现着“价值论”,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梳理游戏理论,关照中国童谣,“游戏性”是童谣这种特殊的儿童文学样式的核心所在。作者认为,童谣是一种儿童“语言游戏”,将语言当作游戏的对象,通过语言这一强大符号载体,展露人类生活的动态画面,使之具有强劲的内在传播力。童谣是儿歌口头上“玩”出来的文学,从语言、体式到内在精神都体现了一种与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游戏性。童谣是儿童释放身心压力的一种手段,是儿童游戏过程的最好伴侣,童谣将游戏精神作为存在的前提与美学品格,其所呈现的感知愉悦、释放快乐的精神内核与游戏精神高度一致。
反映“人事之歌”的童谣,其数最多,创作、改编以及传播都承载着民间老百姓的情感。作者对童谣的解读重在突出其社会叙事的文化意味,不回避用文化的视角来阐释与认识它,将其认定为儿童融入社会生活,尤其是家庭生活,接触成人生活体验、情感表现的重要窗口。有北京童谣云:“檐蝙蝠,穿花鞋,你是奶奶我是爷。”词中舒畅的语义,既来自人世,但又有本质上的不同,各种人情世故在童谣中大都具备,然唱词质朴,妙不可言。
科学知识是人类世世代代积累和传递下来的宝贵遗产,而科技术语因其专业性、抽象性,对于还处于初步认知世界的儿童而言,显得难以理解和识记。作者提出,一首看似简短的童谣包含了诸多认知内容,童谣的好记易诵自不待言,其对于儿童认知系统的教育引导意义确实深刻。因此,童谣在有限的篇幅里运用生动有趣的对话、语词,将儿童吸引到富有动感的科学王国里去,使儿童不仅收获科学知识,在无限的遐想中生成科学理想。童谣具备了指导儿童认知的“科普价值”,很有意思。
由童谣的口语艺术,作者观察到,童谣是有韵的“诗”,追求音乐性,偏重听觉艺术,诗句语音的强弱、长短和轻重以及诗句的押韵、顿歇,都是形成童谣音乐美的重要因素。童谣受口耳传播规律的影响,口语化语汇表达、音乐性追求是其约定俗成的本质特征。周作人曾言:“盖童谣重在音节,多随韵接合,义不相贯,如一颗星,及天里一颗星树里一只鹰,夹雨夹雪冻杀老鳖等,皆然,儿童闻之,但就一二名物,涉想成趣,自感愉悦,不求会通,童谣难解,多以此故。”此言道出了童谣注重音韵和谐,而忽略语言意义的特征,但也不妨碍趣味,就是“无意义”的意义。
人们很早就发现了童谣在儿童成长中的价值,尤其在儿童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作者经过深入爬梳发现,明代以后,童谣始终未能走向蒙养教育的殿堂,与蒙养教育保持着实质性的距离。与相对严苛的蒙养教育相较,童谣无疑就更为随性了。童谣无从考察具体创作者,其传播没有外力的推动,完全自由,其所孕育的教育理念,不依照成人社会的要求,蕴含着教育的理论与育人的规矩。尽管蒙养教育的“学习时空”中有师威的支撑,而童谣的教育影响相对松懈、散漫,但在某种层面上,童谣中仍然表达着蒙养教育的理念与认知,只是其内容方面更加庞杂,形式方面更加活泼,方法方面更加灵活。
该著突出的成就表现在系统梳理与重新建构中国童谣的价值谱系。全书紧紧围绕“中国童谣的价值谱系”这一研究核心,对童谣内涵价值的发展及演变规律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梳理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具体文本进行文本分析,以建立在大量原始文献、童谣文本的研究为基本特色,做到了“论从史出”,多角度、多层面地对“中国童谣的价值谱系”做了深入、细致、系统的评述与总结,最终实现对中国童谣价值承载与本土文化关系的创新叩问。
(作者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