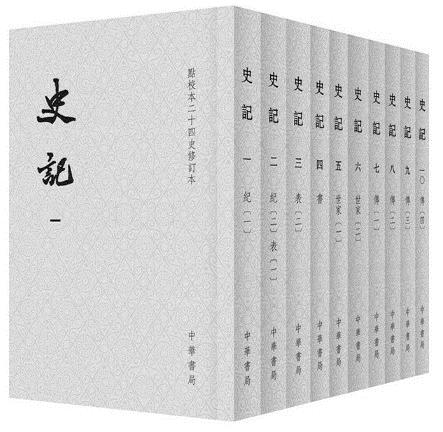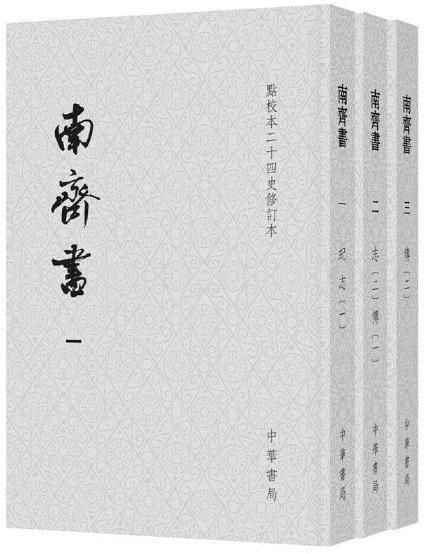本报记者 谢颖
■编者按:
近日,针对不同的阅读需求,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向读者相继推荐了《论语》《史记》的多个优秀整理版本。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籍版本研究对于古籍阐释、赓续文脉,以及读书治学等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报记者采访委员、学者,探讨阐释古籍版本与古籍传承发展。
促进学术研究不断深入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中华文化历经千年传承至今生机勃勃,古代文献典籍是重要的载体。中华古籍浩如烟海,体系完备,世所罕见,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亦是最宝贵的资料。
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沈文凡从大学考入中文系后,一直致力于古典文学研究,而古籍,也伴随了他整个研究生涯,随着学术研究不断精进和深入,他越来越感到文献的重要性。“文学、史学、哲学等人文科学研究都要面对大量古典文献,对文献阅读和解读能力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学术研究的水平。”沈文凡表示,这是做学术最重要的基本功之一,包括版本、校勘、考辨等多种训练。
中华传世文献卷帙浩繁,并且历经千年流传,经过历代的传抄翻刻解读,形成了数量庞大的不同版本,有的遗失了,有的可能累积了很多错讹,版本异文现象非常普遍。沈文凡说,一方面,治学者要有丰富的版本、校勘知识基础;另一方面,版本异文本身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拿古代文学来说,比如韩愈的诗歌创作,其艺术追求不仅体现在通过模仿古体、使用古字、营造古风以纠正中唐诗坛流弊,更是融入了自身好奇尚怪的审美观念和以学问为诗、引议论和文法入诗等开创性做法,使其诗歌作品产生了古奥奇崛中难免生涩晦昧的效果。由此,韩愈别集中所保存的诗歌文本产生了大量版本异文,事实上是对后世学韩诸家的文献校理工作提出了要求,即从基本的文字校勘出发,同时注重对诗意的理解、对创作活动的考证、对诗歌艺术格调的感发以及与韩愈本人思想观念的联系和结合。”
对于“一字之差”是否需要如此精研细磨?“有的人可能会觉得,一个字读对读错没有太大关系,但实际上,有时一字之差,可能理解就不一样,影响内容感情,甚至影响艺术和价值的判断。”沈文凡表示,学术研究要求真,还要在此基础上求善、求美,“字字计较”,研究得越深入和清楚透彻,也就越能吸引读者的兴趣,促进文化的传播。
打造古籍整理精品
古籍整理是让文脉传承、促进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了巨大成就。古籍整理工作需要严谨细致,以“工匠精神”一点一滴钻研,首先面对的就是不同版本的选择和研究。
从2008年开始,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景蜀慧担任中华书局点校本《南齐书》《梁书》和《陈书》的修订主持人,历时13年,完成了这项艰巨的古籍整理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修订并不是在点校本的基础上小修小补,而是重新选择底本,调整通校本、参校本,并在版本选择方面下了比较大的功夫。比如陈书,选用早于百衲本的中华学艺社本为底本,又将存世的全部宋刻本,包括两种全本和4种残本,以及两卷日本平安时期钞本列入通校,加上三朝本、南北监本、汲本、殿本等明清时期版本,《陈书》修订的通校参校本有13种之多,远远超过了当年点校本所具有的版本条件。
景蜀慧告诉记者,早期版本对于正确理解史文、还原史书原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在修订工作中我们由于掌握了相对完整的宋元本和部分早期钞本,有条件和明清以后版本进行系统细致地比对校勘,不仅可以比较确切地判断二者的差异和正误,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探明其致讹之因。”景蜀慧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在《陈书》卷一《高祖纪》中梁敬帝在禅位给陈霸先之前,于太平二年九月辛丑诏书称颂陈霸先的功绩,其中有一句话,“重华大圣,妫满惟贤”。根据文义,这里“重华”指的是舜,那么“妫满”又是谁呢?从《史记》的记载可以得知,妫满乃陈姓始祖胡公满,为舜之后,故为妫氏,舜与胡公满一圣一贤,两句正好相对;而“妫汭”是舜为庶人时居住的地方。根据这类文体骈对的惯例和上下文义,特别是下文列举“亶甫”(后稷之后)、“羲和”(重黎之后)的情况,可判断出此处应为人名“妫满”而不应为地名“妫汭”。“妫满”二字,宋本皆同,但从“三朝本”以下,明清各版本均改为“妫汭”,原点校本亦改作“妫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诏文的原意。所以修订本将此字改回底本,并出校说明版本异文。
另一个例子是《陈书·高祖纪》下,记载陈霸先即皇帝位时下玺书敕州县,敕中云“言念迁坰,但有惭德”。“迁坰”是用商汤代夏之典,文献记载,汤即天子位,“迁九鼎至于亳,至大坰而有惭德。”玺书中的这两句,正是用商汤迁鼎至坰而惭故事,切合陈霸先身份。此处“坰”字,所有宋本包括三朝本皆无异文。但明人或不明“迁坰”之义,从南监本以下到殿本、局本,甚至明本《册府》,都把“迁坰”臆改为“迁桐”。“迁桐”是用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故事,陈霸先取代梁敬帝事,性质完全不同于伊尹放太甲,用“迁桐”所拟不伦,下一句“惭德”更无所着落。但张元济《校勘记》亦以为底本“迁坰”有误,原点校本依从其说法,也据明清版本改字,处理实不妥。修订本亦予以回改并出校。
景蜀慧表示,早期版本具有很高的校勘价值,要以精深的专业训练和学术功底,了解掌握早期版本钞写刊刻补版的基本状况和流传过程,提升对版本正误的判断水平,使严谨扎实的专业研究和审慎细致的文献校勘有机结合,通过精心修订,打造出新时期古籍整理精品。
择“最要之书”“最善之本”让古籍“活”起来
2021年3月3日,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了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整理版本,共40种经典古籍及其179个优秀整理版本,为广大读者遴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最要之书”“最善之本”。这些推荐的经典古籍为具有较强典范性、传承性的古代文化典籍,而推荐的经典古籍优秀整理版本则遵循古籍整理出版规范,质量上乘,覆盖多种类型,注重普及,兼顾提高,努力满足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
古人云,“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对于古籍阅读来说,书目和版本选择非常重要。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刘宁看来,中华典籍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加强古籍阅读推广,能够有力推动古籍“活”起来,走近社会大众,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书香中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以整理本和影印本为主要形式的新印古籍大量出版,让古籍化身千百,已成为古籍阅读推广的关键所在。不过,她发现,一些地方对新印古籍的购藏不够规范,购书经费没有得到很合理的使用,制约了古籍有效推广;还有的新印古籍购藏版本良莠不齐,比如多个《论语》译注本中竟然没有杨伯峻的权威译注版本。如果忽视版本质量,一方面造成浪费,另一方面也难以对读者起到很好的引导作用。为此,今年两会,她通过提案建议,依托省市公共图书馆建设“中华典籍传承基地”,系统购藏新印古籍的“最要之书”与“最善之本”,努力建设对全社会具有示范和引领意义的古籍精品阅读品牌,让古籍的传承推广和阅读出版充分打通,为古籍的精品出版减轻经济压力,让出版社沉下心来多出精品。
“让古籍‘活’起来,加强古籍利用不是单纯把古籍保护起来,而是要让古籍的优秀文化内容真正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走近大众,走向基层,因此要特别关注新印古籍的精品购藏、精品推广。”刘宁表示,“十四五”时期是我国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时期,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真正走近大众,深入社会,要把古籍保护利用和促进基层文化设施布局优化、古籍优秀文化资源共享,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结合起来。她的希望是,古籍的保护利用不断得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断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