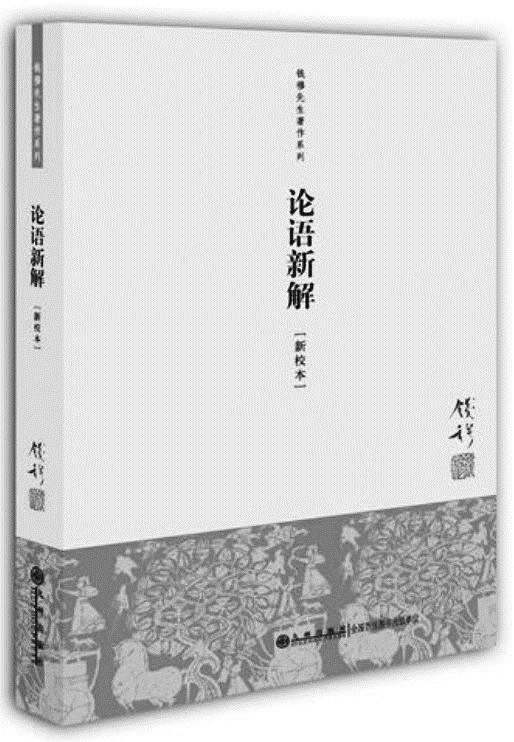1980年早春,中国大地万象更新,远在台湾的祖父恢复了与他相隔30年的儿女们的通信联系,随后即在当年暑假于香港有了一周时间的首次会亲重逢。1981年秋,我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祖父听闻此消息以后,甚为欣喜和安慰,“知道你考进了北京大学,而且有志研习中国古典文学,那是我十分喜欢的事。”“你们的古典文献专业,据你报告,课程应该是注重在本国历史文化的大传统上,这是正确的。”
在我上大学前后,祖父命我给他写信汇报学习情况,并多次给我写回信,对我的读书学习进行具体指导。说实在的,18岁的我对于从未见过面的86岁高龄的祖父的来信,对于来自海峡对岸大学问家的论学指津,那种信赖和认知的程度,也是一点点逐渐建立起来的,免不了荒疏和蹉跎。如今对照当年的谆谆教诲,深悔自己的不够努力;面对近年来网络上比较多转抄的“钱穆给孙女钱婉约的书信”片段,也是不无惭愧,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祖父钱穆(1895-190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高中学历,18岁起在无锡、苏州、厦门等地,做小学、中学老师近18年,这期间他励志勤学苦读,精研学问。1930年,他所写《刘向歆父子年谱》一篇长文,辨章学术,截断众流,显示了深湛的考据功力和思想识断,经同乡顾颉刚先生推荐,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引起学界一时推崇。因而转入大学任教。前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江南大学等校任教,成为民国时期知名的历史学教授。祖父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又到台湾,任教台湾中华文化书院博士班。他生前怀念牵挂家乡,去世后,经家属联系故乡政府、协助寻找墓地,终于在1992年魂归故里,安葬在苏州太湖之滨洞庭西山的俞家渡石皮山上。
《钱穆(宾四)先生全集》甲乙丙三编,共56种著作,近1700万字,有台湾联经版54册和大陆九州版70册两种版本。另外,商务印书馆、九州出版社还出版了很多单行本。近十年来,祖父的著作受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专业研究者以及社会各阶层读者的阅读与喜爱。
切近而言,如何读书,如何阅读中国传统的文史经典,祖父当年对大学生的我的读书指导,如果将它分享给今天更多的青年学生,应该也是有益处的吧。所以,我就权且放下不安的心情,从四个方面分享介绍于下。
第一,推荐四书庄老《史记》七部经典,作为国学入门必读。
大学一年级时,我读了祖父的《论语新解》,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肯定了我将《论语新解》与《四书集注》《十三经概论》并读的做法,并告诉我说:
“《论语新解》则尽可读,读后有解有不解,须隔一时再读,则所解自增,最好能背诵《论语》本文,积年多读,则自能背诵,能背诵后,则其中深义自会体悟。”
“《论语》外,须诵《孟子》《大学》《中庸》,以《朱子集注章句》为主。《庄子》外须诵《老子》。四书与庄老外,该读《史记》。”(1981年12月6日信)
中国古代一向重视熟读背诵功夫,这里的“诵”,应该就是传统记诵之学的“诵”,就是要反复出声朗读,直到熟读成诵,可以背出来。中国历史文化精神寄寓在中国经典和一切古籍深处,若不能深入阅读经典,就不容易认识到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精神与意义价值。反过来,如果对中国历史文化真精神、大传统没有很好的认识,也不能真正读懂中国经典。所以,阅读经典名著名篇,须一读再读反复读,直到成诵;须全读而不宜选读。
《论语》不必说必须通读,《史记》也必须全读:
“读《史记》,须全读不宜选读,遇不易解处,约略读过,遇能解又爱读处,则仍须反复多读,仍盼能背诵。”(1981年12月6日信)
网上有文章传说,钱穆先生让他的孙女背诵《史记》,大概就是由此而发,其实只是说对于“能解和爱读处……盼能背诵”。可惜,大学时代的我并没有很好体会祖父的用心,也没能切实力行地背诵下这七部经典中的多少名篇名章。
第二,诗读全集,散文读名篇,提升自己的心性修养。
对于古典诗词的热爱,从小学、中学自己购买《千家诗》《唐诗三百首》,以及在父亲书架上翻看《唐宋诗举要》就已经开始。我入读北大中文系古典文献学专业以后,也是喜欢“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文学要籍导读”等课程。祖父鼓励说“每日熟诵一两首,是人生一大乐事。”可以先读《唐诗三百首》,上推《诗经》下及陶渊明诗。特别是,他说,读诗建议读专人诗集,挑喜欢的人,读完一人,再读一人。如《陶渊明集》,这是祖父最喜爱和最推崇的个人诗集。读诗集的好处可以想见其人,结合生平际遇,更能品味诗人之心性与思想境界。
读散文,则尽可不读全集,只挑自己喜欢的名篇,如唐宋八大家之古文,选几十篇诵读。能熟读散文名篇,则读一切古人书就容易深入。
“能诵读唐宋诗词亦佳,又贵能推广及于唐宋韩欧八大家之古文,不必通读全集,能选择自己懂得的又喜欢的诵读数十篇,莫急切,只求有入门处。”(1982年7月28日信)
第三,读书为学不可过早地分门别类,以免自设藩篱,自限聪明。
大学三年级时,因为我写了一篇对古诗词中“白日”的辨析文章,信中告诉他,却遭到他的批评指正。他来信说“读书贵能从深处大处留心,如你所举‘白日’二字,并无深意可求,勿多操心,免入歧途。”更从大处说,不要因“专治文学”一念,自设藩篱,自限聪明。
“并须勿分门别类,如专治文学一念,即可限制自己的一切聪明……读书先当求其大者远者,如先限一文学观念来读书,便使自己进步不大。”(1983年1月8日)
学问本来是人生人性与社会历史发展的写照和结晶,古代学术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祖父自己的学问更是兼涉四部,于经史子集都有论著,因此他也被称为“国学宗师”。祖父对于近代以来受西方学术影响,过于重视“分门别类”的学科发展理念是有异议的。他在《中国思想史》等书中,经常说到中国传统思想学术有“通天人,合内外”“推崇博通,不奖励专家”等特点,这些特点和倾向反映在传统中国人的为学追求与学问境界上。比如现在我们看诗人杜甫、文人韩愈、书法家颜真卿、画家吴道子,似乎分别是诗、文、书、画各专门领域的翘楚,其实他们在唐代,却首先都是“蕴蓄充盈”的名相重臣,是一个个博通广大的人。因此,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史学、古代艺术等学科领域,不能忽视这一历史事实,不能仅仅就诗论诗,就画论画。专深为途径,博通为宗旨,祖父的这个思想观念,与现代学术界普遍实行学科分类、培养专门人才的理念与做法,自然是有所区别的。
第四,读中国经典,贵在“切问近思”“反求诸己”。
祖父给我的好几封信中,多处提及阅读《论语》,并把学习《论语》与自我心性人格的成长以及人类世界的发展联系在一起。他说:
“《论语》一书最当反复细诵,盼朝夕在手,日诵二一章即可。自己学问长进,则所得亦随而长进。绝非一览可尽,亦非欲速能达,幸加留意。”(1982年3月30日信)
“《论语》一书,涵义甚深,该反求诸己,配合当前所处的世界,逐一思考,则更可深得。重要当在自己做人上,即一字一句亦可终身受用无穷。”(1982年7月28日信)
大学一年级的我,当时并不能完全领悟信中这些命题和“配合当下所处世界”等说法,但“在自己做人上”,以《论语》里的“子曰”教诲、朱子阐释作为修身准则来要求自己的言行和滋养性情,则多少是有意识这样去做的。我博士毕业后在大学中文系任教,给本科生开设一门“中国文化要籍导读”,所讲内容就主要针对但不限于上述七部国学经典。年复一年,自己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反复研读,加深体悟。同时,也以“切问近思”“反求诸己”来启发我的学生。将知与行相结合,将修身融入求知,关注当下社会文化、人类前途。
2018年,我写过一篇《关于在大学中文学科中加强国学经典教学的思考》论文,发表在《中国文化研究》期刊上,这是我对长年置身其中的大学中文学科教研的一点反思和建议,包括现在的这篇小文在内,都算是我对接受“祖父教我读经典”的一番教育,在40年后向社会的一个回报吧。
(作者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