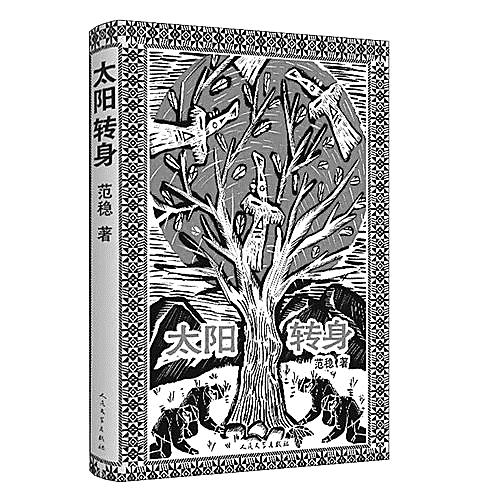2019年夏天,我为创作反映脱贫攻坚题材的长篇小说《太阳转身》,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马关县靠近中越边境的一个壮族寨子马洒寨采风体验生活。这是一个在群山环抱下的幽静小山村。数百年来壮族、傣族、苗族、汉族等各族人民在这里栖息耕作,生存繁衍。从跨进寨门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睛被每一处所闻所见擦亮。修葺一新的干栏式壮族民居,时尚别致的客栈民宿、宽敞气派的中央广场、曲径通幽的青石板小巷、飞檐高扬的老人亭,幽深甘甜的古井,郁郁苍苍的大榕树,荷花绽放的池塘,鲜花盛开的村道,古韵悠扬的农民乐队,歌舞洞天、欢乐活泼的壮族纸马舞,香味四溢、人声鼎沸的农家饭庄。这一切都在向我呈现一个古老少数民族村寨繁荣振兴的巨大变化。
在马洒寨,有一个极具乡村特色的村史展览室,或者说,一个小小的乡村博物馆。那里陈列着最为原始的木质农耕工具,用了几辈人的织布机,布满岁月痕迹的犁铧、风车,前几年才刚刚卸下马背的马帮用具——驮架、马镫、马嚼、皮扣、马铃铛等。这些农具、工具村人用了数百年,它向我们无言地叙说着一个村寨的过往。到今天,科技种田让亩产翻番,微耕机等各式农业机械让耕牛无用武之地,让犁铧进了博物馆,人背马驮被各式汽车取代,千年马帮驿道开拓成柏油马路,私家车停满农家院落;小超市、农家客栈、游乐场、乡村休闲旅游、各式家用电器、移动电话、网络生活,大城市里所能享受到的一切现代文明,这里一样都不缺。
如果我们在这个乡村博物馆里抚今追昔,睹物思史,就不能不为边地村寨的乡村振兴、沧桑演变而感到欣慰,不能不为自己是一名见证者和参与者而感到自豪。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云南省作家协会将一个作家创作生活基地设在了马洒寨,每年派遣两三名青年作家进驻寨子体验生活,感受时代变迁、山乡巨变。作为一名作家,有责任和义务积极投身于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伟大时代,无论是脱贫攻坚战还是乡村振兴、山乡巨变,作家都应该在场,接受它的岁月洗礼,见证它的繁荣进步,并为之鼓与呼。
我生活和工作在一个多民族的省份云南,那里有25个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文化与生态体系,都有自己的创世史诗、宗教文明、英雄人物、生存智慧和爱情故事,更有大时代洪流中沧海变桑田的无数动人故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各民族文化和民族团结进步,是我们的写作优势和取之不尽的资源,每一个村寨的发展演变,每一个普通人的家国情怀,都值得我们去关注和书写。这是发生在乡村的宏大叙事,更是一个作家应该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和使命。一个作家想象力以外的火热现实、生活方式、历史文化、人生经历,发展变迁,已足以构成了小说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新时代的山乡巨变故事,正紧随大时代前进的车轮,在神州大地精彩纷呈地上演,我们云南也概莫能外。由于历史和地域方面的原因,这里民族众多,又地处边疆,社会发育相对较晚。在脱贫攻坚战打响以前,云南全省贫困面积大,贫困程度深,脱贫攻坚任务之难、之艰巨,可想而知。在我创作长篇小说《太阳转身》时,我所去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就是一个集边疆、民族、贫困于一体的地方。因为地处边境一线,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还处于战争状态,它开放的时间比内地晚了10余年。许多村庄都在极度贫困线之下,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连一段水泥路都显得奢侈。20世纪90年代我们去边境一线出差都还要开“边境通行证”。在脱贫攻坚战中,这里的人们向大山要路,向石漠化要地,他们像当年参加边境保卫战那样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在这个和平的年代,我在那里却感受到了战争的气氛,感受到了上战场的豪迈,感受到了向命运挑战的勇气。脱贫攻坚这样划时代的伟大战役,作家首先应该在场。如我们的文学前辈柳青、周立波、赵树理等文学大师们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有些写作模式,作家在场永远正确。
我在边境一线采风时,走访了十几个边境一线的村庄,时常和那些经历过战火历练的人们打交道,他们当年是战场上的英雄,现在是脱贫攻坚的主力和领路人。这些人身上散发出来的优秀品质和英雄气,时常在感染着我,激发着我的写作欲望。我沿着边境线采访,踏勘当年的战场,营房、堑壕、哨卡、猫耳洞、界碑、国门,这些曾经也是我们的青春记忆。我总认为一个中国人一生中应该去看看我们的界碑,在边境线上走一走,了解一些边疆地区的人文和历史,这样会更加深他的疆域概念和国家认同感。国境线虽然是无形的,但它在每一个边地人心目中又重如千钧。正是这些边地人,多年来默默地承担着戍边守土职责的同时,也在坚韧顽强地改变着家乡的面貌。他们不应该贫困,边境线上的村寨更不应该贫困。每一个村口,每一条村道,都是国门所在。边疆脱贫了,边境线就稳固了;边境线稳固了,国家就安宁了。
因此,文山州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就显得特别具有典型意义,或者用文学的话语来说,特别具有辨识度。没有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没有乡村振兴战略的大力实施,就没有边疆地区的山乡巨变。我把文山州的壮民族文化和脱贫攻坚作为一个新课题来研究和学习,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也是一次挑战。
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圆满胜利之际,我看到了边境线上的村庄天翻地覆的变化。我看到了一条公路对一个闭塞的村庄的重要,一个惠民政策对一片地区的改变。其实,一个人,一个村庄最重要的改变,是思想观念的转型和提升,是精神文化的丰富与文明,是最古老最传统的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完美拥抱和结合。这就是我所希望看到的山乡巨变。因为在今天这样一个跨越式发展的时代,人们的观念必须接受现代文明的洗礼。
云南近现代史中有一段历史颇能说明观念革命的重要。1910年的秋天,一列法国殖民者的火车,用野蛮的力量撞开南中国的大门。这条依据中法两国不平等条约修筑的从越南海防通向云南昆明的铁路,曾经是民族的创伤和屈辱,但同时,也给遥远封闭的边地带来了蒸汽机文明。在铁路修筑之初,它被视为洪水猛兽,遭到了当地人的强烈反对,甚至不惜武力抗争。可是当火车运行起来后,习惯于乘坐轿子马车和人背马驮运输方式的人们逐渐领悟到了工业文明的强大和不可抵御。仅仅在法国人的火车开通4年以后,云南的士绅阶层便筹划修建我们自己的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民营铁路。尽管它因轨距窄车体小、速度慢而被人们戏称为“小火车”。但它是我们民族自尊自强的象征,是从马帮时代进入到蒸汽机时代的飞跃,体现着高原人走出大山的勇气和智慧。到今天,它已成为一笔弥足珍贵的工业文明遗产。
我曾在澜沧江大峡谷里看到这样一幅神奇的图景:布满马蹄印的千年马帮驿道在山谷里蜿蜒盘旋,到江底需靠溜索和渡船摆渡;在古渡口上方是20世纪70年代修建的公路桥,在公路桥两侧,则分别是本世纪初建造的高速公路桥和普通铁路桥;而在接近峡谷两边山巅处,是一座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一部分、正在建设的通往东南亚诸国的高速铁路桥。是的,高原人已然进入高速时代。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正穿过一个又一个美丽的乡村,给他们带来梦幻般的变化。上世纪初我们自修的铁路被称为“寸轨”,时速仅为10来公里,一百年后我们的高速铁路,则达到350公里。这段峡谷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云南高原百年交通变迁,它们像苍茫大地上一个巨大的隐喻,昭示大时代的沧桑巨变,也促发着我的创作灵感。
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应该是一个渴望生活的人,渴望进入到大时代的“大生活”中,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小生活圈子。当我们用文学的魅力再现出时代的风采时,我们的写作才会有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著名作家,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